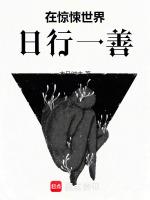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刺杀反派失败后东起丹暮 > 第376章(第1页)
第376章(第1页)
商嫣嘴唇抖了抖,很快冷静下来,“湘州那边知道了吗?”
“驿站正要往湘州传信呢。”
商嫣目光渐沉。雍州的消息能顺利到建康,得益于李挽离开前重组的驿站人手。但建康的消息,可不一定那么快能到湘州。她用驿站寄回去的家书,十天半个月都到不了。
雍州情况不容乐观,怕是一刻也耽误不得。
思及此,她当机立断,转身回屋,抓起一件斗篷,便往后院牵马,“等不来了,我亲自去一趟湘州,你帮我们看好宅院。”
商嫣没有去过湘州,她至今为止连建康都没有出过。
新都初立,又逢战乱,一路上,商嫣都在担心,关城一盘散沙、乌烟瘴气,根本无暇顾及她。
然而,她看见的是崭新壮阔的城池,是金妆素裹的街巷、衣香鬓影的游人,是安乐祥和的一幕幕,她总觉得心里怪怪的,很不是滋味。
商家表哥商予泉来城门接她,先带去酒楼用饭,那酒楼缀的秀灯甚至都是金子做的;再带去茶肆用茶,那戏茶的女娘个个腰肢绵软、婷婷袅袅。
商嫣心急战事,一顿饭吃得很不是滋味,着急忙慌想要回府。可商予泉说,湘州多水渠,阡陌交通,画舫盛行,定要带她去取经。商嫣坐在船上,听那呢哝小调,吹那湖面微风,总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这真的是战乱之下的大梁吗?为何这里的人,脸上都是微笑,就好像只有她才知道危险,就好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周游大半日,终于在日暮时回到商府。商粲和往常一样,坐在庭院里作画,只是如今,换了宅子,他的画桌更大更气派,是一整块澄澈无暇的美玉,让人挪不开目光。
商嫣走近他的身边时,商粲正落下最后一笔,大气磅礴的骏马图跃然纸上。商粲满意的观赏片刻,“晓得回来了?”
商嫣福身见礼,不欲再耽误时间,直接讲出雍州的消息,“女儿是为雍州战事而来。雍州吃紧,人马不足五万,粮食药材告急。如今消息还在路上,但雍州将士等不得了,女儿想请阿父向陛下进言,增援雍州。”
商粲脸上的悦色明显褪了下去,他将笔杆一搁,“你为了画舫,坚持不跟我们南迁,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是为了说这些?”
商嫣咬咬牙,“画舫关系诸多女娘的生计,女儿不能弃之不管。雍州关系着全大梁的安危,女儿也不能置之不理。”
商粲,“我大梁还没有弱不经风到这种程度。五万燕北军,十万精兵,怎么可能败。老夫不回信你一面之词。”
商嫣有些焦急,“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十五万人马如今只剩五万,父亲难道还不愿承认大梁的颓势?父亲难道还在幻想着胜利吗?”
“颓势?什么颓势!”
商粲眼睛一瞪,白眉气得一股一股,别过头去收拾画稿,不愿再搭理人。
商嫣绕到他正面,磨他许久,“阿父,时代已经变了!”
“没有!”
商粲怒得一拍镇纸,
“上次你就是这句话,劝我接受科考。结果呢?是,时代是变了,但礼教秩序,绝不会变!大梁就是最昌盛的,区区边陲小国,从前他们连天子真容都见不到,如今还想打败我们?痴心妄想!”
“阿父!”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行军用兵之事本就不在我的职权之内,前次派遣十万援军,陛下已经极其不满。他们自己无能,十万雄兵都能败仗,也不反思自己,还想着求援,陛下不会同意的。”
商嫣颇有些痛心疾首,“战场千变万化,如果能赢,有谁愿意牺牲呢?陛下短视,担心军心不稳,不敢调太多军队增援,可阿父有没有想过,唇亡齿寒,雍州失守,建康无人,湘州之祸难道还远吗?”
商粲沉默不答,商嫣忍不住扬起音调,“阿父怎忍心纵容陛下袖手旁观,使故国沦陷,使百姓失所!”
“够了!”
商粲情绪过于激动,一大把白胡子都在发抖。
”
你……你知道什么……”
他咬着牙,翻来覆去,欲言又止,最后抹了把皱巴巴的眼眶,
“多说无益。为父教育你不要抛头露面,为夫着令你早日成家,你听从了吗?你连纲常伦理都守不住,老夫凭什么要听你在这里大言不惭的谈论家国天下?”
商嫣嗓子哑了,“阿父……您……竟这样想我。”
商粲将手一背,转过脸去,不再看她,“不成家便不成家吧,既然回来了,就在府里好好呆着,府外的事一概不要问,老夫也不会问。”
商嫣许久都没有做声,只是身后传来三声额头撞地的闷响,然后是坚定的脚步声,头也不回的向府外走去。
商粲微微仰头,痛苦的微微阖眼。他了解自己女儿,别看商嫣温柔如水的倾国模样,骨子里却是极其刚烈的牛脾气。她决定的事,绝不可能妥协。
商粲叹了口气,“回来!”
商嫣勉强停步,留下一道挺直的背影。
商粲无奈的捏了捏眉心,“过完年再走。”
商嫣想了想,算是默认。
如今权贵都在关城,商粲虽不帮她,但示意她留在关城,倒也方便她奔走求人。
只是这些人的冷漠,超出她的想象。商家门客所剩无几,他们还算礼貌客气,虽然爱莫能助。拜访戴家纪家时,她直接就被请回。
就连最应该出手相助、最有可能出手相助的陆公陆怀章,也只跟她说了一句话,“陆蔓已经不是陆府女儿,生死与我无关。”
商嫣不明白,权贵为何如此事不关己,仿佛遭人践踏的不是他们的国土一样。想找王迟帮忙,他整日忙于关城建制,等了几日,连面都没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