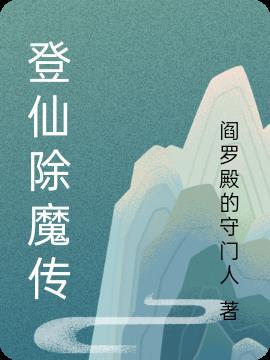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渡渊的诗句 > 第100章(第1页)
第100章(第1页)
>
当初司徒宥齐要去参军,要离开洛州到京州去,老两口就是一万个不同意。什么威逼利诱,能用上的手段全使了个遍,可最后呢,还是没能拦下司徒宥齐,他还是去了,这一去就是这么多年。
而今司徒宥齐又说自己要为了心上人终身不娶,态度比起那时候的似乎还要更加强硬,这下看来,是怎么样都不能更改了。
可离家参军和终身不娶比起来,终归不是一个量级的事情,老两口还是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什么?终身不娶?!”
父亲猛地一拍桌子,将茶盏都震落,碎了一地,迸裂声却丝毫盖不住他的怒意,“婚姻大事,岂可儿戏?且不说你与那小姐并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已经成了亲,她死前无后,作为夫家的要续弦,那都是合情合理的,你却要为了她终身不娶?”
“是。”
司徒宥齐的回答掷地有声,“从前我不娶,是怕让好人家的女儿做了寡妇。而今我不娶,您便当我是做了旁人的鳏夫……”
父亲气得抄起夫人手边的茶盏,朝着司徒宥齐砸去,打断了儿子大逆不道的发言:“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司徒恩齐正好从外头回来,差点被飞来的茶盏误伤。
“爹爹,你这是做什么?”
司徒恩齐避开一地的碎瓷片,从袖带中掏出手帕来,蹲在司徒宥齐的身边,小心翼翼地替哥哥擦拭脸颊被瓷片划开的伤口。
其实这么点儿伤,对于一个在战场上看惯了刀光剑影的副将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但在司徒恩齐一个女儿家看来,就是做女红的时候,手上被绣花针扎了一下,都痛得不行,脸上落了这么一道伤口,怎么可能不疼呢?
一向是慈父面孔的父亲,却少见地对司徒恩齐凶了起来:“你莫要管,回屋里去。”
司徒恩齐被凶,却不怕,因为她知道父亲是个纸老虎,只会装凶,根本舍不得真的训自己,于是继续说:“哥哥是做错了什么,刚回家就要被爹爹教训。”
父亲厉声喝道:“你哥哥做了全天下最大逆不道的事情,你不许替他脱罪!”
“哥哥在战场上军功赫赫,为国,哥哥是忠臣;这些年来,哥哥的俸禄大半都寄回了家,那些银子都是哥哥用血换回来的,咱们却跟着沾光,为家,哥哥也是个一等一的大孝子。因着哥哥的军功,咱们家在洛州都跟着脸上有光,司徒一族都视哥哥为好样的,怎么到了爹爹这儿,反倒把哥哥贬成了大逆不道?”
司徒恩齐伶牙俐齿,倒噎得父亲母亲都说不出话来了。
其实还是因为司徒恩齐说得没有一丁点儿错。
这些年来,司徒宥齐虽是没能在堂前尽孝,可也是一点儿没有亏着过家里。司徒家能过上今日这般的日子,能在洛州城成为名门望族,其中一大半儿原因都要归功于司徒宥齐。
除了今日司徒宥齐所说的要终身不娶一事,实在再挑不出第二点错处来怪他了。
父亲无话可说,最后只能赶人——眼不见心不烦。
“你走吧,滚远些,莫要再来我面前碍眼了。”
父亲说。
母亲却说不出这样的狠话,只道:“待你爹爹消了气,再回来吧。”
司徒宥齐不顾满地的碎片,重重地扣了一个头:“爹爹,娘亲,等你们的气消了,孩儿再来看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