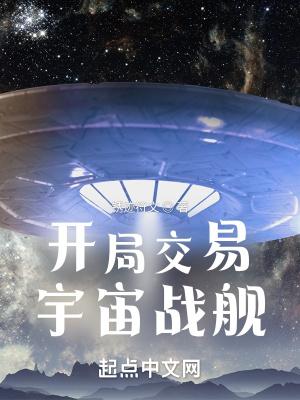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岁绥棱县有多少ktv呀绥棱县有多少ktv > 第65章(第1页)
第65章(第1页)
云泷亦侧眸看了眼成珺,心里来气,大声道:“是啊,快回去吧,免得有人乐不思蜀啦!”
淮鸢憋着笑,瞅瞅云泷,又瞅瞅陷于思绪什么也没听见的成珺,真是当局者迷。
窗外已打二更,长街只余更夫一人执锣,一人提笼,在寂静黑暗中行走,偶有虫鸣窸窣,二人左顾右盼探查后,又壮着胆子阔步向前。
淮鸢阖紧窗扇,桌前幽暗烛火噼啪作响,在静默中格外醒目,她轻吐气,晃悠火焰倏忽化作一缕悠然烟气,盘旋向上,屋内归于一片黑暗。
淮鸢提裙,迈步推开房门。
成珺本已躺在床榻,只因心事困扰,翻来覆去迟迟未入睡,房门被敲响的第一下,他还以为精神错乱,出了幻觉,直到一下下敲门声连续响起,他又忍不住心想,怕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寻到他头上来了,忙将被衾拉过头顶,自欺欺人地当作什么也没发生。
然门外的敲门声大有一种你不开门,我便不停歇的意思,少年的脾性很快被激起,血涌上头,再顾不上吃人的恶魔传说,猛地翻被下床,甚至连鞋袜都未来得及套上,唰地一下由外自内拉开门。
满腔恼火在见到门外挂着歉意笑容的貌美女子时,瞬时又如被强行熄灭的火焰,气还没消,势先去了。
“……淮姐,你大半夜的是要吓死我啊!”
成珺憋红了脸,气不打一处来,探头在门外四处望了望。
“就我一个人。”
淮鸢道。
成珺不知想到哪里去,瞬时向后跳了几尺,双手捂在胸前:“我,我不能背叛叔公!”
淮鸢:“……”
她没理会成珺的异想天开,趁着他跳开,走近屋内,转身关上了门。
这一举动,入了成珺眼中,更是加重心中猜测。
淮鸢自顾自坐在桌前,倒了杯热水,偏头一瞧,成珺竟还一副良家妇女受侮辱的防御姿态站在很远的地方,无语片刻,道:“你站那么远干嘛?我又打不过你。”
成珺委屈巴巴挪近:“可叔公收拾我还不是小菜一碟。”
“……和王爷有什么关系,我和你掰扯这些真是没事找事,我来是想问你件事。”
“哦,问事情啊。”
成珺这才松了口气,回到床边套上鞋袜,“哎,你早说啊,吓得我都失礼了。”
淮鸢青葱指尖摩挲杯壁,温声道:“你今日为何执意要见灵姑娘?”
成珺嬉笑面容稍逝,手指一顿:“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知道什么,对吧?”
淮鸢眼中发亮,抬眸看向他,“有关昭德王府?还是王爷?又或者是,舒王?”
啪的一声,布鞋自成珺手中不慎滑落,摔在地上在寂静中发出不小的声响,他瞪大双眼,满面写着难以置信。
淮鸢心跳落空,喃喃道:“竟是与舒王有关?”
能让成珺这般在意的,定不是什么小事,若不是与昭德王府有关,那大抵便是与晏屿青有牵连,然灵姑娘风靡大成之时,晏屿青尚且年幼,很难想象出二人能有什么纠葛,那么便只剩他的宿敌舒王了。
其实淮鸢也只是直觉猜测,其中也有很多其他的可能,也许成珺偏偏就是格外关心大成大小事,又或者他也只是单纯兴致来了,想听听灵姑娘的琴音,因而她说这话,也是在诈他,不料,这么容易便诈出来了。
成珺知晓自己上当,瘪嘴委屈道:“你怎么能这样,可千万别和旁人说这件事啊。”
“行,我知晓事情轻重,一定不和别人说。”
淮鸢拍着胸膛打包票,“不过,前提是你得和我说清楚,他们有什么关系。”
“那怎么能行!”
成珺下意识反驳道。
淮鸢气急:“当然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到时候我去问晏屿青,他一定也会告诉我的,你现在说或者不说,我都会知道,为什么不让我早些知道呢?”
成珺被这一通歪理说得脑袋发晕,叔公会不会同她说,他不清楚,可叔公对淮姐的偏爱是有目共睹的,他不自也犹豫起来,还真顺着淮鸢的说法斟酌起来说不说。
淮鸢见此法还真能成,忍不住煽风点火:“而且,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想当面问灵姑娘?如今她已经不在,若是你同我说,我助你一起调查推理,岂不是你我都心想事成?”
成珺肉眼可见被说动,淮鸢又缠了片刻,他心理防线崩塌后,终于开口:“说好了啊,这些都只是一些流言,尚未经过考证,你可别当作事实四处传播。”
淮鸢少不得又是对天发誓,又是拉钩约定,他才安了心缓缓说来。
“听闻在舒王十多岁的年纪,曾经在昌德镇住过一阵,那时正是灵姑娘名声最望的时候,舒王是她的座上宾。”
当年,先皇已近半百,朝中对于太子人选成日争个没完,除去早早远离朝中是非,安心待在川源城的肃王并无夺嫡心外,其余数位皇子纷纷有着身后站队大臣簇拥推举,而舒王兼具野心果决,更是围拥着无数贵族大臣。
然他便是在这如日中天的时刻,忽地远离了京城这权力中央,跑到大成南部小城住了几年。
当时有人说许是他厌倦争斗,也有人说许是当时的皇帝不喜朝中夺嫡风气,他是识时务避风头的。
当然,后来证实了,舒王从未消过争斗之心,当年他带领进攻京城的兵,便是南部郡王们的兵士。
“我听见霜儿姑娘是灵姑娘的女儿,我忽地就想起这事了,当年便有流言传出,舒王在南部小镇有私生子,我猜想,霜儿会不会是舒王的孩子。”
成珺红了脸颊,想来这样如同妇人的碎言碎语并不符世家公子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