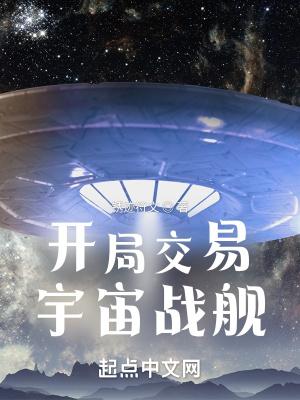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陈米麒个人资料图片 > 第15章(第1页)
第15章(第1页)
阿弟还很挑食,但是我在,他就什么都吃,他说哥哥陪吃饭很开心,所以什么都喜欢吃。从那会起,阿弟就像是我新长出来的尾巴一样,一直跟在我身后东跑跑西走走的。有一天他问我,如果有新的爸爸妈妈要来带走我们该怎么办,我说当然是走啊,难道你想在福利院待一辈子吗?可他一个小屁孩哪懂什么一辈子,他只是说那我能不能和哥哥一起走,我说不行,要看新爸妈愿不愿意,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就问他你以后想叫什么名字,他想了很久,用树枝在地上写了一个字,他说院长妈妈组织演讲的时候说过英雄都是宁折不弯的,他也要当英雄,所以以后他要叫‘折’,我说这个字不好,像大人们常说的那样,是犯忌讳的。他不管,说英雄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还问我说那哥哥要叫什么名字,我说都可以,如果有新爸妈的话,他们给我取什么名字我都会很开心。
我十二岁那年,福利院里来了两个想要领养男孩的家庭,我和阿弟就是最终被挑选上的孩子。那两个家庭,一个姓李一个姓陈,那天阿弟穿着李家爸妈给他带来的新衣服,那是件中间画着图案的红色棉袄,穿在阿弟身上特别好看。李家爸妈牵着阿弟的手,阿弟的眼睛眨啊眨的,他看着我,问我怎么不穿新衣服,问李家爸妈是不是哥哥也要一起走,李家爸妈哄他说没有宝贝,哥哥要去其他爸妈家。可阿弟却一下子就放开了李家爸妈的手,哭着闹着要我跟他一起走,他哭得好凶,比以往被噩梦惊醒的时候还要凶,我突然觉得我哄不好他了,因为他坐上小汽车离开了很久我都还能听到他在哭。
再过了几天,我也被陈家人领养走了,他们家住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叫同水村。刚到他们家里的前两年我也是过过好日子的,我有爸妈可以叫,有新衣服可以穿,还有书可以读。我坐在祠堂里,一页页地翻开那本一年级的语文书,直到那时我才发现原来书是有香味的,是一股水稻的香味。读完一年级,家里新生了个男娃,我很高兴,因为我又有了一个弟弟。可是慢慢的,我就不怎么高兴了,因为我没书读了。陈家人告诉我,书要留给弟弟读,让我留在家里照顾弟弟,帮忙干活赚钱,我答应了,因为那是我的家。干活其实不辛苦,没书读也不要紧,可是我的身上开始出现各种跌倒和碰撞出的伤痕,很多时候旧的还没好,新的就把旧的给盖过去了,陈家阿妈说我走路不当心,为了让我学会专心就罚我只能吃半碗饭还不准夹菜夹肉吃,然后我碗里的饭就再也没有盛满过。
后来陈家阿爸经常出去打牌喝酒,我记得那天晚上风雨很大,我给他开门的时候被他那浑身的酒气熏得吐酸水。他是个黝黑的西北汉子,力气极大,我被他抓住时完全没有反抗能力,他把我扔到一个柜子旁边,从背后圈住我,我被他压着只能将上半身趴到柜子上,接着我就听见他在解裤子的声音。那个柜子是用木头做的,高度只有当时的我胸口那么高,只要动静一大它就会吱吱呀呀的响,陈家阿妈大概也是被它吵醒了,我看到她拿着煤油灯出来,可是很快煤油灯就不见了。我还看到我指甲里藏着白天干农活时留下来的黑垢被柜子上的木刺硬生生劈开,那时我就在想,可能以后我的指甲里都藏不了脏东西了。直等到邻居王婶家那只病殃殃的公鸡开始叫唤,我才回到草席上。我想睡觉,可眼睛一转,就看见地上有两个像红又像黑的圆点,我知道,那是血。你们说前段时间去搜过我家,我想,你们应该也已经见到过那个柜子和那张草席了吧?
隔天我照旧去干农活,只是干得没以前快。我也不怎么爱说话了,就只是用眼珠子看。渐渐的,我发现村子里的外来女人和孩子越来越多,村子里的人管她们和他们叫做货,于是我明白,我其实也是货,是陈家的货。经历了这么多事的一年,我也才十八岁。
第二年,我被送到村子最东边的屠宰场里干活,那里很臭,很脏,活儿也很累人,但是我干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暂时不用再回到那个家里边去,我只需要住在屠宰场旁边搭着的棚子里,再按时给陈家弟弟交学费就行。可是没干几个月,陈家阿爸就来让我偷些猪蹄回去给弟弟补身子,我说不行,被发现了我要被打的。他就骂我是个杂种。当天晚上的风仍然很大,他呼哧带喘地跑到棚子里找我,还是让我给他家偷猪蹄吃,我不肯,然后他又做了和那晚一模一样的事,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棚子脏,也是第一次有了想要砍死他的冲动。
但我还是偷了。不过我总是偷那些别人不要的猪下水,偶尔逼急了就剁点猪蹄肉拿给陈家阿爸,我很笨,以为这样就不会被发现,直到我被屠宰场老板打到鼻子止不住的流血。我又回去干农活了,村子里的货还是很多,有些旧货整天疯疯癫癫的,有些旧货我就再也没有找到过。我忘记是哪一天,村子里又来了一批新货,动静大到让我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然后我和陈家阿妈说我要到村子外头去赚钱,说我要赚好多好多钱给弟弟娶媳妇,她笑着答应,然后监视了我两年,我也很听话的把钱都交给他们。大概是觉得放心,他们就不怎么爱管我了,我便找了家有电话的铺子,花了两毛钱打了一通报警电话。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陈米在讲这些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就像在和人讨论今晚要吃什么一样平静,语气也只有在提到他阿弟时有所起伏,反倒是我这个看客先有些坐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