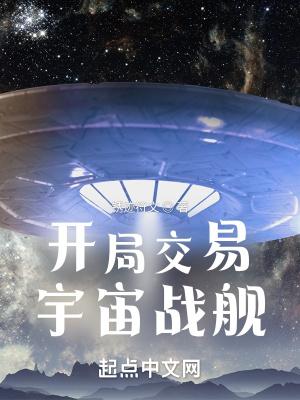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千千锦瑟戏中织免费 > 第26章(第1页)
第26章(第1页)
里面传来孟王爷温厚的声音,“你进来吧。”
我推门进去,看到孟杼玑站在孟王爷旁边研墨,那孟王爷低着头手执毛笔在那里写字。孟杼玑知道我进来轻抬了一下头,看了看我,说,“二哥哥找我有事?”
“不是二公子,是千织,千织想来求求三小姐。千织想代画荷罚跪,千织有一次看到画荷那方帕子上绣的花样很是好看,就偷偷拿了做式样想自己绣。画荷一时找不到帕子才没有把它给袁少爷。”
我说完这番话,孟王爷也抬头看我。我看他目光中很是惊诧,接着死死地盯着我,我被看得心里发毛,只得讷讷地低下头。
我听到孟杼玑的声音,“哦?是这样?那好,你现在去替画荷跪着,今日不用回芊蔚轩了!”
我心里长舒一口气,心想画荷起码没事了。转念想到我自己,我心中寥然,从袁府跪到孟府,我真真正正是命途多舛、生不逢时、饱经风霜、造化弄人。
“谢谢三小姐。千织这就去跪着。”
我赶紧告退,转身打算走,听到孟王爷喝了一声,“站住!”
我从刚刚起就被孟王爷看得一颗心七上八下的,他这一声“站住”
差点没让我立马趴下。我定在那里,小心地说了一句,“王爷,还有什么吩咐?”
那孟王爷放下手中的毛笔,对旁边三小姐说,“杼玑,你先回去,我有事要问问这个丫环。”
三小姐更是不愉快了,娇嗔道,“爹爹,你要问个丫环什么事?她私自藏了我的帕子,理应去前院里跪着。”
孟王爷蹙了蹙眉,这表情和孟二公子真正是如出一辄,很有威严道:“杼玑,你先下去。”
三小姐看了我一眼,甩甩衣袖走了。我心中很是担心画荷,小心地对那王爷说,“王爷,千织连累画荷替我跪着,心中有愧,可否请王爷允了千织去替画荷受罚。”
那王爷走到我跟前,细细地看着我,问我,“你姓什么?叫什么?爹娘何处?”
我不知道这位王爷是打的什么算盘,只得如实回答,“我叫尹千织。我爹娘都是这清洲上的小百姓,做些小食生意。我年幼丧父,前年娘亲也病逝了。”
“你娘已经死了?!你娘可是叫初之?”
王爷听了我话表情更是凝重,往前迈了一步,甚是急切地问我。
在袁府的时候,那位袁老爷也曾问过我关于这位初之,莫非真是袁老爷和孟王爷的故人?这次我不想再扯谎骗孟王爷一次免得再惹来一顿罚跪。我轻摇了摇头,说:“王爷,我娘姓王,不姓初。我从未听说过初之的名字。”
王爷听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嘴里喃喃道,“不可能,你们长得这么像……”
接着他一把拉住我,和我说,“你和我去个地方!”
顺势就要往外走。
我心中一急,赶紧和那孟王爷说,“王爷,画荷还在代千织受罚。王爷可否让千织领完罚再去?”
那位王爷顿了顿,走到门外叫来了位老管家,和他说,“你让前院跪着的那个丫环先免罚罢。”
接着,他看着我说,“现在你和我去吧。”
我跟着孟王爷急匆匆地出了孟府,沿着条小路走到一处旧屋前。王爷敲了敲门,一位老妇人开门,她看到王爷,叹了口气道,“王爷,你还是请回吧。老妪实在是无以为告。”
孟王爷赶紧叫住那老妇人,“丁大娘,我孟某今日里不求其他,只求大娘帮我看看这孩子可是初之后人。”
那丁大娘听了王爷的话,凑过来看了看我,面有难色,半晌不语。
孟王爷在一旁有些焦虑,此时全无王爷那股子傲气,他语气稍软,颇是诚恳,“大娘,你就看在孟某从堰城到清洲这些年的份上,帮孟某这个忙。孟某此生恐是也再见不到初之一面,如若这孩子是她的女儿,孟某定会视如已出。”
说到后面,孟王爷竟是有些颤巍。
那丁大娘轻叹了口气,她走过来抓着我的手,道:“小姐,请随老身到里屋来。王爷,请一并进屋来用些茶。”
我跟着丁大娘走到里屋,感觉大娘的手微微有些哆嗦。我用伸手摸了摸她,对她说,“大娘,这位初之夫人可是与我有什么渊缘?”
我看见那大娘点了柱香朝窗户处拜了三拜,然后回来坐在我身边,对我说,“孩子,我曾答应过那位姑娘决不将此事告于他人。但这十余载,孟王爷为了那姑娘从堰城寻到清洲,也真正是个痴心情种。如今,我只能有负姑娘当日所托。
我甚是不解地望着这位大娘。她走过来问我,“不知小姐背上腰后方可是有一处扁形胎记?”
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那大娘看着我,说:“小姐,可否让老身一验?”
我于是很是配合地把衣裳褪了让那大娘瞅了瞅,我迫不及待地问那大娘,“大娘,有么?”
我听到她略有些哽咽的声音,“小姐,你便是初之姑娘之女。”
前尘旧梦缘(二)
这位大娘甚是诚恳地和我说我娘另有他人,我震撼不已,这不过弹指的时间,我就多了个后妈。我很是莫明其妙,“大娘,我娘姓王,我不认识这位初之夫人,大娘何以用这个胎记就认定我娘是这个初之?”
“小姐,你是老身亲手接生的。你这枚胎记老身记得清清楚楚,形状好似扁豆,当时初之姑娘说为你取个小名叫小扁。且你现在的模样与初之姑娘那时的模样如此相似,不是母女,哪来这么巧的事情?”
听到说我的小名叫“小扁”
,我对这位初之夫人顿时好感俱无。我此时满心疑虑,“大娘,但我从未见过这位夫人,而且我打小便和我娘在一块。如果这位夫人是我娘,那她为何将我送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