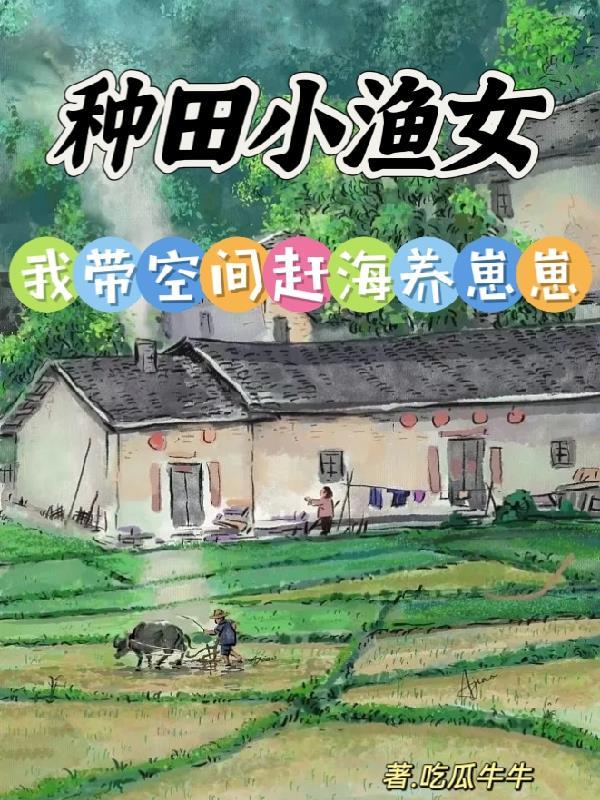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难琢txt > 第13章(第3页)
第13章(第3页)
“就像刚才那样……我可以帮你进货,算账,打杂,”
方应琢说,“不用给我工资,之前给的房费我也会照付。”
像刚才一样?在工作间隙趁机对雇主进行xing骚扰吗?
我在心里哂笑了一声,听听,多新鲜啊,这个城里来的小少爷不仅想帮我打工,还要在打工的时候倒贴钱,如果全世界的打工人能有方应琢这个觉悟,资本家大概在梦里都会笑出声。
既然我已经转变了想法,又没有那么快想扔掉方应琢这块烫手山芋了,于是,我顺阶而下,应道:“行啊。”
说是这么说,我也不会真的让方应琢做什么事。我虽然称不上是个好人,但也没到周扒皮那个程度,不至于泯灭了自己的良心。
当晚,方应琢打开笔电,准备继续修之前拍摄的图片,然而,就在他打开相机包、取出相机时,才现相机镜头磕碎了一角,应该是昨晚打那一架时弄坏的。
这次来粟水,方应琢带了两台相机,一台用于日常摄影,一台用于录制视频,除此之外,还有一台大疆mavic3pro,但方应琢平时拍照片比较多,最常用的还是这台被磕碰了的相机。
方应琢小心地拆卸下受损的镜头,拿起手机搜了些信息,然后对我说:“秦理,明天我需要出门一趟,去c市。”
c市就是这个省份的省会,我猜方应琢是想更换一个新镜头,只有c市这种大城市才有相应货源。
我当然没什么异议,毕竟方应琢来粟水本就是为了拍毕设,当然是他的正事更要紧。我点点头:“嗯,去吧。”
只不过从这里去c市挺麻烦的。粟水镇位于深山腹地,即便去省会也要转换几次交通工具。先要坐大巴车从粟水到县城,再坐绿皮火车从县城到c市,大概需要一整天。
第二天一早,方应琢就从商店离开,我睡眠浅,清楚地听见了方应琢的脚步声。等到方应琢走后,我也下了床,开始洗漱、换衣服。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竟莫名觉得这间又小又破的屋子有些空荡荡。
其实,方应琢是个很安静的人,他就算在屋子里,也不会出什么声音,但我这时才清楚地意识到,就算方应琢再安静,有人和没人的差别竟然这么大。
走到桌前吃早饭的时候,我现方应琢还给我留了一张便利贴,上面的字迹非常漂亮。便利贴旁边还放着一颗方应琢常带在身上的海盐太妃糖。
——很快就回来。
嘁。多此一举。难道我很想他回来吗?我吃掉糖果,把糖纸和便利贴揉成了一团。
我坐在桌前罕见的了会儿呆,就连自己也很难说清到底在想什么。十几分钟后,我换上外出的衣服,锁好商店大门,去了粟水镇的车站。
车站只有一个售票窗口,我走过去,看了一眼车次表,对售票员说:“买一张到洛城的票。”
洛城就是距离粟水最近的县城。想去省会的人通常都从这里出。
上午和下午各有一趟车,我付了钱,接过车票看了一眼时间,上午那趟还有二十分钟车。候车大厅的人寥寥无几,方应琢在其中异常惹眼,他垂着头,大概是在看手机。
我悄悄戴上了连帽衫的帽子,莫名地不太希望方应琢现在注意到我。
也许从商店来到车站可以算作一时冲动,但直到买完了票,我也没搞懂我到底是在做什么。
想见方应琢吗?不想,看见他就烦躁。想去c市吗?当然也不想,毕竟出门这一趟我还少挣几天钱。那到底是为什么?
手里的车票也被我攥得皱皱巴巴的,我快步走向检票口,趁方应琢还没有起身,先方应琢一步上了大巴车。
其实,这不是我十八年来第一次做这种头脑一热的事。至于上一回,与其说是冲动,本质上是去赴约。
在我上高三的时候,非北与我聊起报考大学,对方建议我考虑一下都的那几所学校,非北列举了很多条优点,最后在信的末尾说,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想见你。
现在一回想,这话说得非常令人牙酸,肉麻程度和方应琢有一拼,不过当时的我只觉得十分喜悦和感动,我研究了都每一所双一流高校,给非北回信说没问题。
一星期后,我又收到一封新的来信,非北提议在我高中毕业的暑假时就见上一面,然后他附上了见面的时间和地址,是七月中旬的一个日子。非北说,如果我不方便,不去也没有关系,但他会在那里等着我。
我没有立刻拿定主意,没给非北准确的答复,后来,六月份高考失利,七月份看着其他人有了录取结果,我去悬崖边的那块空地吹了很久的风,那时我的手依然动不了,又得知了秦志勇的死讯,有那么一瞬间,觉得活着确实没什么意思,不如跳下去,一了百了,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什么烦恼了。
这样的想法愈演愈烈,我的身体又向着悬崖边缘走了几步,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脑海中开始走马灯,我想起以前的许多事,想到奶奶,已经没什么印象的母亲,秦志勇,胡雨霏,周敦行和死去的严小禾……最后想到非北,以及那个我还没有应答的邀约。
等等……现在离非北说的那个日期只剩两天了!于是我掉头就跑,没拿任何行李,跑到粟水车站,乘大巴到洛城,又坐了整整三十五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都。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山,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么庞大的城市。如果让很久以后的我自己去形容,我总是会想到《海上钢琴师》中的19oo,他曾经也想过走下那艘生活了一辈子的船,可他望着船下未知又复杂的世界,到底没有踏出最后一步。
都于我而言,就是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地方。
人潮汹涌的地铁站里,我无法避免地陷入露怯的境地,因为从未乘坐过这种交通工具,也不知道该怎么买票,自己一个人站在机器前捣鼓了很久,结果票还买错了方向。不过,这座城市里的人行色匆匆,并没有人会在意一个路人的窘迫。
第二天,我准时在中午十二点抵达非北说的地点,是一家位于书店中心的咖啡店。据非北所说,他那天会穿灰上衣和黑裤子,手里拿着我寄给他的信,如果我见到他,就能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