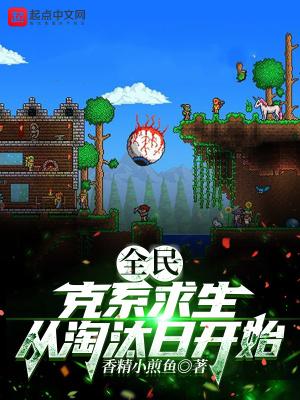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金笼雪衣不似桂酒 > 第30章(第1页)
第30章(第1页)
姜献弯腰取剑,忍着不去看她的眼:“你是想问我,去多久,远不远,时间够不够你逃跑,是吗?”
“那我告诉你,不够。”
嘉穗小脸一白,她后腰无力塌坐在地上,姜献将她颓然的样子尽收眼底,全盘接收她的绝望和失落,含笑大步往马车外走出。
他在外留了很多人,嘉穗便是生十对羽翼也绝跑不出他精心布置的围场,正因自信她已是掌中之物,他的神态从容冷静,边走边忽然想到什么,回过头,昳丽的面容衔起一笑,“嘉穗,如果你这次还想跑,最好不要表现得太明显,起码不能在今天。我的忍耐一向有限度,方才我已忍耐得够久。”
他指她刚才那一巴掌,笑意渐深,“你再跑,我真的会做死你。”
帘帐质地轻软,徐徐落下盖住姜献的身影,他留下的话语却像刀锋一样横在门前,绝了嘉穗此刻逃跑的心思。
她现在又能跑到哪里去。
嘉穗眼睛眨了眨,用力瞪到酸涩的程度,才疲软得垂下眼睛,抱着膝盖,蜷缩在羊毛毯上。
她若有若无的闻到他身上的檀香,起初以为是马车内的熏香,慢慢才发现是从她的长发、衣袖和裙摆上传来的。
他热衷于在她身上留下他的味道。
浓郁的檀香腥甜如血,嘉穗解开如瀑的长发,她皱眉,用手一点点梳理长发上沾染的檀香,哪怕没什么用。
不知道姜献还能耐着性子陪她演多久,他的确比常人更有耐性,但对她从来不是。
他必须时时刻刻,确保她被他占有着,才会像喝了安神汤一样温驯。
马车外传来大片的嘈杂和打杀之声。
嘉穗惊了惊,想到刚才姜献的离开,她确信法灵寺附近一定出了什么乱子,幸好南家家眷只有她一人来了,祖母姐姐她们都在家中待着,可还有裴元悯和裴家的女眷在。
嘉穗撩起车帘,不等她看清外面的景象,一个清秀的宦官笑眯眯走上前,挡住了她的视野:“六姑娘切莫着急,可是想家了?也是,天色将晚,是时候归家了,等大人回来,立即送您回家。”
嘉穗不理他,扭头再看,很快又被人挡住,她苍白的小脸滞了滞,正过来,皱眉看着那宦官。
“公公,请让开。”
见她居然认出自己身份,宦官心中暗暗一惊,知道她不像寻常的小姑娘好糊弄。
他讨好的笑了,小心翼翼的问:“六姑娘是饿了,还是渴了,想吃什么,我去给您买来。”
嘉穗恬淡的笑了,仔细看她笑容冷淡的带着讽刺,“如果我没有猜错,法灵寺是出乱子了,我不是聋子,听得见刀剑之声,这种时候,你问我饿不饿,我吃得下去吗?”
她有些疑惑的歪了歪头,像实在不懂姜献和他这一群手下的做派,“法灵寺到底出什么事了?人命关天,你不要骗我。”
早在姜献下马车时,车夫就将马车泊在更隐蔽安全的地方,松柏遮掩着大半马车,嘉穗的心脏却像枝头摇摇欲坠的松果触不到底。
那宦官瞅了瞅她,看她面容严肃,不像个好糊弄的,只好斟酌着挑不严重的说法答她:“近来东番不太平,有东番人混入流民之中,意欲挟平州望族的家眷生乱。”
嘉穗垂下脸,心想难怪。
难怪这不年不节的,南北也未听闻灾事,不见多少流民,怎的忽然要施粥。
见她不动了,宦官便想将车帘放下,免得让她看见血腥之事。
谁知嘉穗忽然仰起头,清婉流溢的面庞忽然生出几分神采,紧紧盯着宦官,一字一句问:“陛下是带人救他们去了对不对?”
宦官连忙微笑着答:“正是,陛下仁德……”
不等他说完,就听见嘉穗坐在车内,柔柔的声音像林间的清风,清冷冷传来:“刀剑无眼,听闻东番人尤其残忍彪悍,陛下……会死吗?”
宦官被她问得差点栽倒,他重重一抹额头,嘴唇抖抖:“六姑娘,这话可不兴说,陛下知晓东番计谋,早有准备,更有真龙护体,怎会被贼寇所伤,这样的话,六姑娘年幼,日后再也不要说了。”
他好心劝嘉穗,嘉穗没应声,她靠在车壁上,有些疲倦的垂了垂眼,想:
……可惜了。
被软禁在车内,四周有侍卫把守,嘉穗再不挣扎,安安静静在车上待了半个时辰,便听见有马蹄声响起,紧接着传来宦官的惊呼:“陛……大人,您这是怎么了,身上为何有这么多血?”
坐在马车里闭目养神的嘉穗猛地站起,夺门而出,她漂亮浓黑的乌发在半空划过一道秀丽的香弧,提裙的动作和嘴角扬起的弧度,同时僵在看见姜献的那一霎。
姜献手提长剑,长剑有血滴落。
他身上黑袍染了血也看不出,倒是苍白的脸庞溅上少许鲜血,使得他浓郁的眉眼更加炫目。
此刻他正漫不经心站在那里,任由侍从为他清理身上沾染的血迹,更替长袍。
尊贵矜立,如在宫中。
察觉嘉穗失落的视线,姜献转眸看她,他不动声色品尝了她的表情半晌。
她既隐忍又失望的表情太有趣,让他忍不住勾唇,扯下染血的披衣掷落在地,露出尚算干净的长袍,随手将剑交由侍卫,朝着她气定神闲的,一步步逼近。
“为何是这种表情?嘉穗。”
他替她叹息了声,喉咙深处却漫上笑意,“我毫发无损,你是不是很失望?”
服软
嘉穗双手低垂,提起的裙摆复又落下,不能逃跑,这个动作就全无意义。
她手扶车门,目光闪烁的看着一步步走近的姜献,她看得见他眼中的志得意满,那是一种姜献从不会对外、只会对她露出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