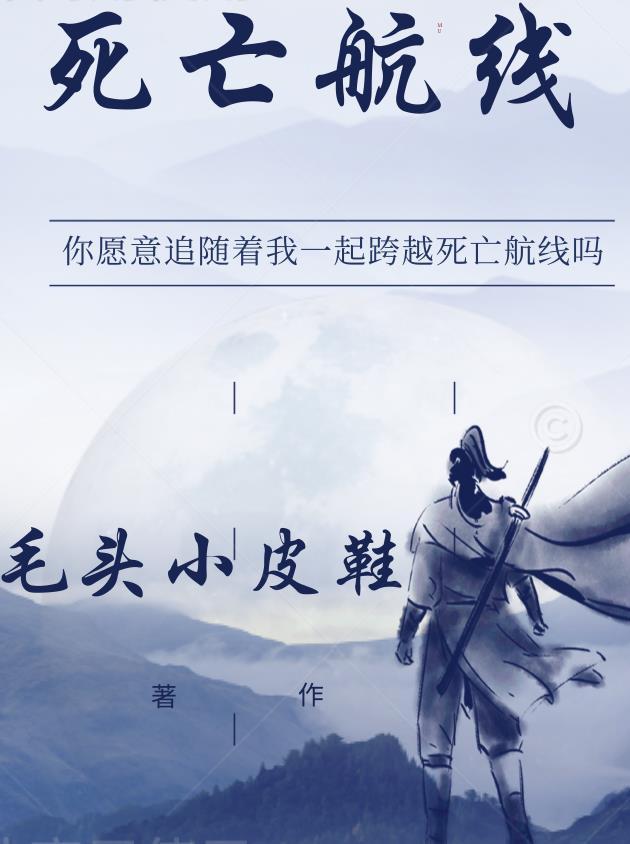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渝欢姜厌辞免费阅读 > 第63章(第2页)
第63章(第2页)
而他只穿一条西装裤,皮质腰带总是松松垮垮地束在腰间,好像她轻轻一扯,他就能呈现出最为原始的状态。
在他密不透风的吻落下时,她总能及时捕获到他别样的炙热,这感觉很奇怪,就像它握住了源源不断的生机。
每到那时,她还会想起汽水是什么滋味的,咕噜噜,冒着气泡,吞咽进喉管,呛得有点疼,但会让喜欢自虐的人欲罢不能。
……
言欢感觉到自己脸上湿漉漉的。
那是长时间被夺取呼吸无法适应沁出的生理性泪水。
女人难以在力量上同男人较量,性|爱也是,她眼睛里全是水务,他却干燥得过分,仿佛一个不受普通欲念影响的情场老手。
片刻,她改变了这种认知。
他的目光基本都是温和的,清明到装不下多余情绪,现在不一样,他多多少少受到了欲望的支配,涌上时,那股冷淡劲无一生还,尽数被冲垮,眼底剩下烧灼的火焰,险些烫伤她。
在他的气息开始紊乱前,言欢下意识摆出了扭捏的姿态。
反应过来,只觉自己好笑。
卖乖的次数太多,她差点都信了自己是真的乖。
瞥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她贴了上去,空气霎时变得稀薄。
哪怕这会的主动权不在她手里,过了电的酥麻感还是密密匝匝地侵袭而来。
渗出的汗液乱七八糟地留在对方的肌肤上,勾画出一副最莫名其妙的毕加索画。
这画只完成了一半。
是梁沂洲喊停的。
他提前透支了欲望,代价是中途清醒后铺天盖地的后悔。
落到另一个人的眼里,不好看,也让人心凉。
如果他不在离开前抛下一句“对不起”
的话,气氛或许不会如此僵。
言欢是真愣住了,感觉自己又做了一场梦,偏偏残留的触感太清晰,做不了假。
她的胸膛还在剧烈起伏,胸口上沾着汗液,分不清是谁的。
梁沂洲打算在客房将就一晚,这是最好的冷静方式,但他没有,去外面吹了会风,偏偏又忘了五月底的夜风里也含着燥热的因子,体内的那天热意差点卷土重来,逼得他裸着上身在18度的冷气站了足足十分钟。
他拿这折磨人的十分钟,仔细回忆了下他离开前最后接受到的眼神,不及他的狼狈,却有着他难以匹敌的复杂。
她站在那里,像嵌进悬崖岩石缝隙里的一朵蒲公英,也像空谷里回荡的一缕风,广阔又忧郁。
又过了会儿,梁沂洲关了空调,由西而东,走到主卧门前,抬
手曲指,几秒后又放下,直接开了卧室门,言欢已经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