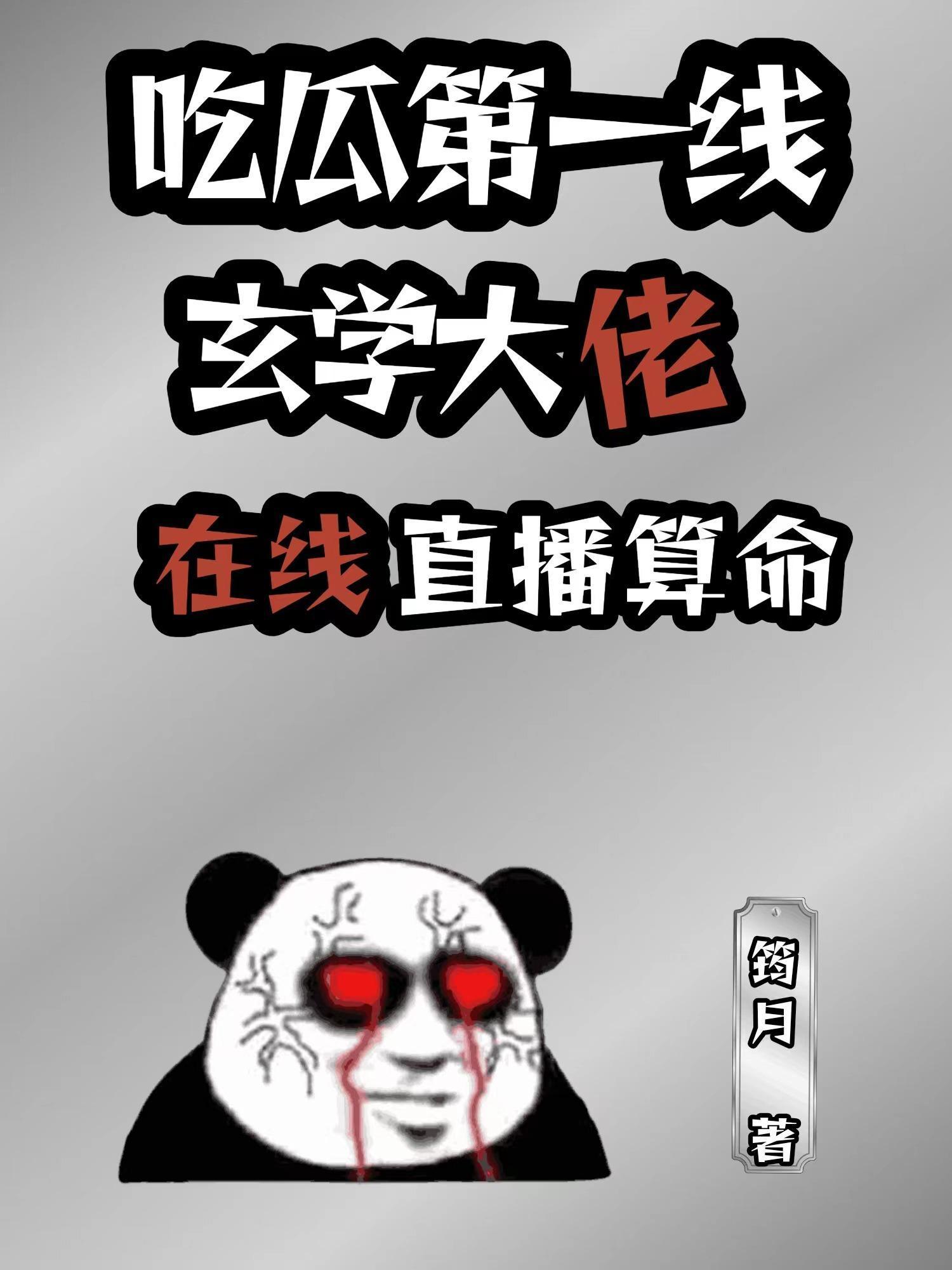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花月记忆 > 第9章 我要留下来(第2页)
第9章 我要留下来(第2页)
“拯救?”
陶月儿再次蹙眉,问道:“他需要旁人拯救吗?”
他有手有脚,身体健康,心里光明,没有半点需要旁人帮助的样子。
阿音却大力地点头:“伶哥哥是我们所有人之中,心理疾病最严重的一个!你别看他表面上没事,其实比谁都敏感,所有的愤怒都积压在心里,这样下去,迟早会爆的!”
陶月儿半张着嘴,愕然道:“此话从何说起?”
阿音的神色间浮起她这个年纪不会有的凝重,似是有不得了的惊天大秘密。她拉着陶月儿坐在厨房门槛上,四下看了看,确定无人靠近了才幽幽道:“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你可千万不要传出去。”
陶月儿用力地点头:“我一定不说。”
“事情是这样的——”
阿音思绪飘渺,说出了一个闻者流泪,听者伤心的惨痛故事。
花伶自幼生长在官宦之家,父亲是一方太守,权力颇大。只可惜,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皇帝之后,花父便因派系站队错误之故被流放岭南,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而他的母亲因模样姣好,被新太守据为己有,后因不堪受辱,没过多久便投河自尽。花伶也沦为官奴,被派去了戏楼,终日咿咿呀呀,讨好上位之人。他原先的名字也被抹去,只单名一个‘伶’,是以‘伶人’之意。
而他原本也还有一门未婚妻子,因他家道中落而与他断绝关系,与新太守的儿子定了亲。大婚之日来临,太守府却抬了两顶大红花轿进门。一顶是刘老爷家的千金,一顶里头却是五花大绑的花伶。
没错,新太守的儿子不仅看上了花伶的媳妇,还看上了花伶。从此,他与未婚妻一起嫁给了一个男人,过上了更加暗无天日的生活,可谓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但就算如此,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轻生。他立誓要等到父亲回来父子团聚。后来,花伶虚与委蛇,终于获得太守一家的信任,然后找了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逃了出来。因为慈幼局瘟疫所没人敢来,他便隐藏在这里,一待就是大半年。
“怪不得……”
陶月儿听后,喃喃自语,半晌回不过神。
“怪不得什么?”
阿音奇怪道。
——怪不得花伶那么讨厌我。
——因为他见不得旁人轻生。
他的人生从云端零落尘泥,都从未想过放弃,而她除了内心受创,其实也没吃什么口头,却扬言再也不活了。
难怪他对自己如此冷漠。
陶月儿看着这满院子得了疫症仍不放弃生命的孩子,她突然想起初见花伶之时,他曾说过的那句话:
——“你所轻易放弃的今天,是已故之人梦寐以求的明天。生命来来往往,每一天都是不可复制再得的人生。你,真的打算就此放弃?”
他其实是想劝自己不要轻生吧。
陶月儿也终于能明白,花伶为何小小年纪,面上总是无一丝笑容,冷漠成了他的代名词,寡淡成了他的座右铭。
他独身孑立,比月亮的清晖还要皎洁。没有什么比在人生最绝望时候与美好相逢更令人感到庆幸的事了。因为经历过黑暗,所以更加向往光明。能积极面对人生的人,他心存着希望,无论生活面对的是艰难抑或困苦,他都不会活得太糟糕。
花伶就是这样的人。
傍晚,陶月儿在山脚下找到花伶。此时的他从山上采药下来,正准备给地里的芋头浇水。
“我不想死了。”
陶月儿追上前,拖住花伶的衣袖,郑重地说:“我想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孩子们。”
傍晚的阳光照耀在山头,有一种别样静谧的美。
花伶回头,淡淡的看了陶月儿一眼。
陶月儿的目光坚定,眸中带着一抹消失了许久的光亮和期冀。
花伶眼中的轻蔑渐渐褪去,良久才终于微一颔,淡淡地说了一个字: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