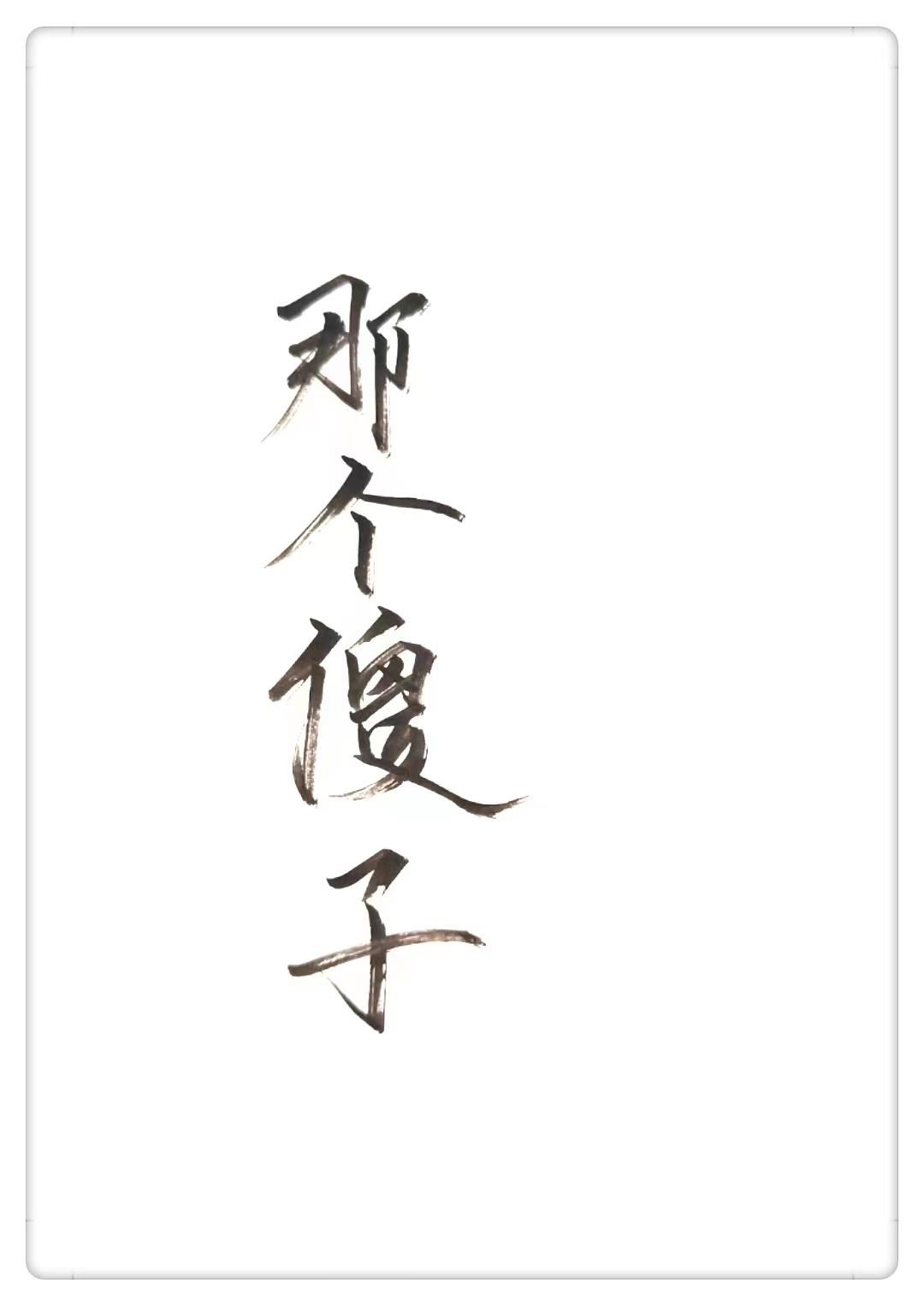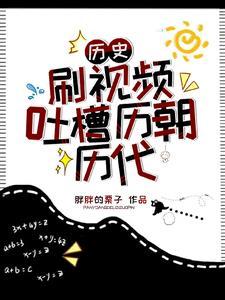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病秧子王爷穿越妃 > 第11章(第2页)
第11章(第2页)
谢承阑眉尾微扬,觉得他天真,忍不住道:“怎么,你当真以为是尧安王余党?”
“不然?难不成你在王都还有仇家?总不能是谢承翟那厮要害你吧?”
邓钰宸知道,尽管他们兄弟俩间有再多看不惯和龃龉,谢承翟也不至于要置他于死地。
退一万步讲,谢承翟真要除了谢承阑,断不可能是派些贼来,而该是栽赃泼水之类,借刀杀人一击致命的,要让谢承阑必翻不了身的那种。
谢承阑只道:“那些余孽本就成不了气候。说不定我真有什么不知道的仇家呢?”
邓钰宸眉眼一挑,道:“难不成你抢了人家媳妇儿?还是说……你这几天惹了哪家姑娘又将人辜负了?!人家回去后伤心欲绝,越想越亏雇了人来杀你?”
没等谢承阑应声,他又自顾自道:“在北庭的时候就没见你和姑娘亲近过,也就和小蕊妹妹走得近一点。真这样该说你什么?铁树开花?还是蓝颜祸害?”
“……”
谢承阑想了想,低头沉默了会儿,忽然牛头不对马嘴道,“你知道红月楼吗?”
“都城里最热闹的那个酒楼?”
邓钰宸眼里升起八卦之星,嘴角止不住上扬,胳膊肘轻轻碰他,“难不成那姑娘是红月楼当家的女儿?”
“不是。”
谢承阑一本正经,“里面有个说书先生,讲的东西又臭又长,你知不知道?”
“嗯?”
邓钰宸神情疑惑,不明白他怎么就扯到说书先生了。
谢承阑道:“我觉得你可以去红月楼谋事,把他换下去,救一下那些个听书人的耳朵。”
“……”
“说说你吧。”
谢承阑说回正事。
“我?”
邓钰宸偏开脸装糊涂,“我有什么好说的。”
谢承阑道:“你就甘愿留在王都了?”
“邓翡了那么大的犯事儿,累得我父亲被卸了官职,邓家上下还在人人自危,皇上到现在嘴里都没一句准话,你觉得我有其他办法吗?”
邓钰宸无可奈何,“就算我父亲官复原职,你也知道,他不可能再放我去北庭了,顶多给我谋个闲散官当当。”
谢承阑当然知道其中利害。
只是邓钰宸自小同他在北庭历练,兄弟俩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费了十余年才混到长史的位置。
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就这样待在王都,只得被埋没,他惋惜也痛惜。
“该说不说,现在这条命还能留着都是万幸。”
邓钰宸劫后余生舒了口气,“只是可惜了钰翀,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落得这么个下场。幸而元安王有心相助,我都不敢想在城墙上看见钰翀头颅的样子。”
谢承阑听到后半句有些不舒服,微微皱眉,似为不解,道:“你怎么三句不离元安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