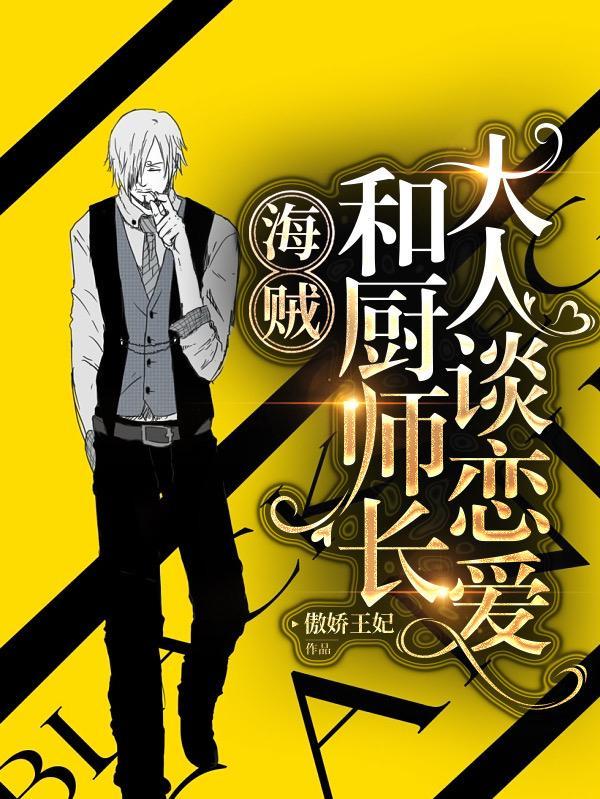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知更鸟蛋蓝 > 第17頁(第2页)
第17頁(第2页)
「我不知道。」
上尉凝視遠方,吸吮自己的牙齒,頓了頓足。接著他向愛德華點點頭,對他的班長低聲說了幾句話,班長是陪同上尉前來的下士,然後他們舉手敬禮。兩人離去時踩得腳下白雪咯吱作響。
「就這樣。」愛德華說,依然望著蓋布蘭。
「是。」蓋布蘭說。
「稱不上是什麼調查。」
「對。」
「誰想得到會這樣?」那隻圓睜的眼珠毫無生氣地盯著蓋布蘭。
「這裡隨時都有弟兄叛逃,」蓋布蘭說,「他們也沒辦法調查所有的……」
「我是說,誰能想到叛逃的竟然會是辛德?誰能想到他會做出這種事?」
「對,可以這樣說。」蓋布蘭說。
「他竟然臨時起意,站起來就逃跑了。」
「對。」
「可惜那挺機槍不能用。」愛德華的語氣既冰冷又帶有諷刺的意味。
「對啊。」
「你也不能呼叫荷軍哨兵?」
「我叫了,可是已經太遲,天色很暗。」
「昨晚月光很亮吧。」
兩人面面相覷。
「你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嗎?」愛德華說。
「不知道。」
「不,你知道。我從你的表情可以看出來。蓋布蘭,為什麼?」
「我沒殺他。」蓋布蘭的目光緊緊鎖在愛德華那隻獨眼上,「我試著跟他講道理,可是他不聽,然後他就跑了。我還能怎麼辦?」
兩人呼吸凝重,都在風中弓著背。寒風撕碎了他們口中呼出的水汽。
「我記得以前你臉上也有過這種表情,蓋布蘭,就是你在碉堡殺死蘇聯士兵的那個晚上。」
蓋布蘭聳聳肩。愛德華伸出一隻手搭在蓋布蘭的手臂上,他手上的無指手套覆蓋著冰晶。
「你聽好,辛德不是個好士兵,他也許連個好人都算不上,可是我們得明辨是非,我們必須維持一定的標準和尊嚴,你明白嗎?」
「我可以走了嗎?」
愛德華看著蓋布蘭。希特勒在各個戰線不再取得勝利的傳言,這時已開始對他們產生影響。然而挪威志願軍的數量仍節節攀升,丹尼爾和辛德已由兩個來自廷塞市的青年士兵取代。年輕的面孔不斷冒出來。有些面孔你會記得,有些面孔一等到他們陣亡你就忘了。丹尼爾是愛德華會記得的面孔,他心裡清楚。他也知道,再過不久,辛德的面孔就會從自己的記憶中被消除、被抹去。小愛德華再過幾天就滿兩歲了。他不願意再繼續往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