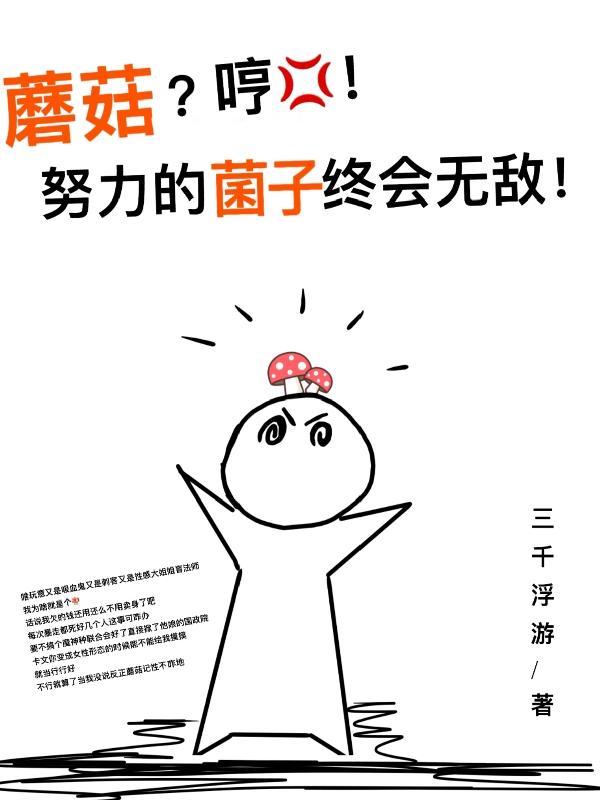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亲爱的太子殿下英文 > 第68頁(第1页)
第68頁(第1页)
這一句話,就叫程束回想起了當年之事,頓時讓他心中難安。
他垂了眼,隔了一會兒才道:「當年……是我的錯,若能早把方令棋安置好,也不至於出這等事情。」
烏塗爾不忍見他這般自責,當即探了身子,親在他面頰上:「如此良辰美景,殿下就這般感傷懷秋嗎?」
「你……」程束微微一怔,又恍惚笑了:「好,你可莫要後悔。」
一方溫泉,最是能溫潤人心。烏塗爾前幾日被折騰出來的酸痛尚未全消,這會兒被熱水一激,倒是說不出的爽快來。
程束一直在他身邊,見他舒服得喟嘆,喉頭微微一動。伸出手去探他的肩膀:「瞧瞧,連這些地方都是傷痕。」
「殿下嫌棄不好看的話,我就找些藥,把它們都抹平了。」烏塗爾道。
程束不語,想起這四年來,自己動輒安插圖龍衛進去西北大營。那些人回稟來的事情雖然不同,卻都說烏塗爾打起仗來幾乎不要命,哪裡危險去哪裡。有那麼一二回,當真就快要丟掉性命。當時程束接到急報,看見這些話語的時候,心裡又痛又恨,想著當即就要親自去西北,把烏塗爾抓回來,好讓他不再受一點委屈。
可他冷靜下來,又只好作罷。想著如果這就是烏塗爾心之所系,他橫插一腳,又算得了什麼?再者當時上京內因為德王刺殺一事,仍舊沒能肅清餘黨,這會兒叫烏塗爾回來,保不齊又成了誰攻擊的靶子。
可現在不同了,德王被壓,皇帝幾乎成了空架子,對蔑洛族大捷……這一切的一切,都在預示著程束,可以把人搶回來了。
而他也的確做到了。
心中這麼想,程束難免難耐。他側過身子貼住烏塗爾,和他耳鬢廝磨,又靠在他側頸上,含含糊糊道:「李參將,本宮封你當大將軍。」
烏塗爾初嘗那事兒,自然禁不起挑撥,聲音都怪了起來,一邊哼一邊道:「哪……哪有靠這般當上大將軍的?」
「那你說,想要什麼?我都給你找來。」程束根本不看他,只想把他都吃進腹中。
烏塗爾攬住他,低聲道:「我想要和殿下在一起。」
「在一起一輩子。」他被程束激得戰慄,可這話照舊要說:「就像我送的那對兒琉璃盞一樣。」
與此同時,程束正巧掐了掐他,指尖又划過。烏塗爾冷不丁得哼了一聲,最終沒撐住,直接滑進水池裡去了。
他剛想探出頭,卻被人貼住嘴唇,口中被渡了一口氣。
烏塗爾不甘示弱,將太子也扯了進來,下一刻反客為主,啃了上去。
直到兩個人覺得都要窒息,才從水中冒頭。程束氣息不穩,道:「好,好個小狗,咬人真疼。」
烏塗爾瞧著他,神情恍惚,眼睛裡的想法根本不加遮掩:「明明是殿下先招惹我。」
「哼……」程束喉間發出低沉一聲,又是貼著上去:「喜歡我的人太多,烏塗爾,你覺得自己憑什麼和我一輩子?」
「憑殿下也喜歡我。」
這話十分自信,程束笑了起來,忽然伸手將人從水中撈出來:「溫泉雖好,不宜多泡。」
烏塗爾對他的舉動心知肚明,也不說話,只是抱著他。
在溫泉旁的小室里,烏塗爾才發現太子給他帶的金鎖環是做什麼的。那東西一邊連著他,一邊又扣在床欄上,根本叫人脫不開。
他一隻手吊著,本有些難受,可程束卻照顧他照顧得很好。兩個人都像是燒紅的熱炭一般,旺到深處,一觸即燃。
這回可比在鄭府的時候要熱烈很多,或許因為是在太子自己的地盤上,又或者是因為太子聽了烏塗爾想和他一輩子的話。
而烏塗爾也不知道自己對著太子,竟然有了那麼大的膽子。等好不容易太子給他解開金鎖環,他又翻身,把太子翻在下頭。他能感受到太子按著他,而他直起身來,簡直要成了一汪水。
他俯身,忘情的吻著太子。
太子低聲罵他:「不是小狗,是小狼崽子。」
烏塗爾渾然不覺,還笑著說:「是殿下的小狼崽子。」
幾經魂不守舍,終是精疲力竭。
小室中溫度有些高,可兩個人並在一起卻不覺得熱。屋外就是溫泉,倒也不需要內侍們來端水淨身。只不過需要落落汗,以防染了風寒。
烏塗爾疲累得要命,卻仍舊是不肯睡過去。他在太子懷中,滿是饜足。
程束也沒好到這麼地方去,在他耳邊私語:「沒想到,狼崽子這麼野。」
「殿下也不似看起來那般高潔。」烏塗爾反唇相譏,說完,自己先笑了。
「那都是外人看的。」程束道:「我什麼樣子,你不都知道了嗎?」
烏塗爾嘆道:「那時候鄭湘文給我講風月記,我瞧裡頭形容美人,都說膚如凝脂、眉目如畫,現在想想,用這詞形容殿下,卻是有些不夠了。」
他說著,臉一紅,又道:「不知我什麼福氣,能得殿下垂青。」
程束微微一惱:「原來早早對我有非分之想,當初臉紅,也是為了這些吧。」
「嗯。」烏塗爾也不遮掩,大大方方講出口:「若不是殿下對我說喜歡我,我也反應不過來,原來當初殿下那般對我,也是存了心思的。」
程束被他戳穿,也只是道:「那又如何?不過是彼此彼此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