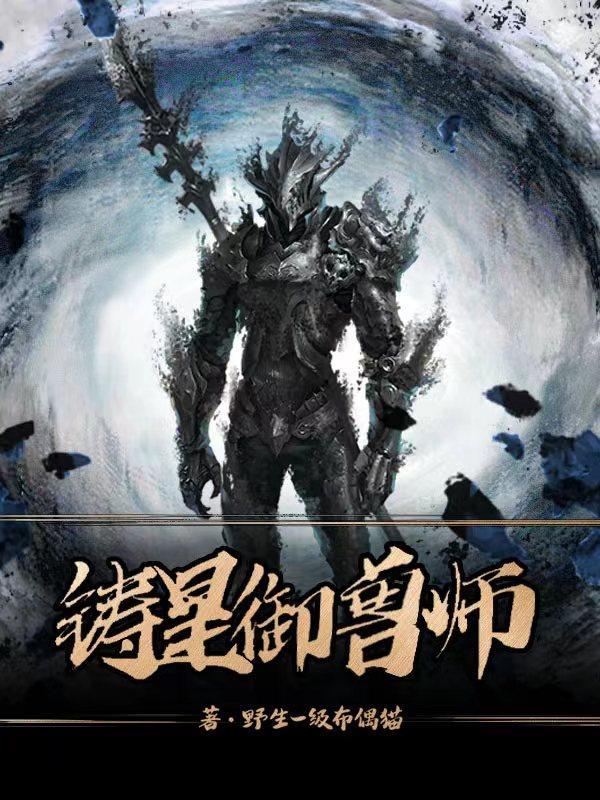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不小心创亖了娇妻系统推文排雷 > 第71頁(第1页)
第71頁(第1页)
「符斟其實也挺不錯的,他話多,最會哄女人開心,但你可千萬別陷進去,這人大概也就是玩玩……」
「哥,」阮如安忽然打斷道,「當年是我執意要嫁給賀天賜的,所以我在賀家吃苦賠錢,我活該,我認命。但現在我也確實不再愛他了,我們……真的不能離婚嗎?」
阮如川沉默了。
「我明白了,」阮如安失落道,「阮家的顏面最重要。」
「……不是顏面的問題。」阮如川像是見不得妹妹傷心難過,下意識地脫口而出。
但下一秒他就反應過來,硬生生將後面半句咽了回去,猶豫了好半晌才悄悄附在她耳邊說:「爸爸不讓我多說,但我們不讓你離婚,和顏面之類的沒有任何關係……你這個婚你確實離不了……至少現在離不了。」
現在,離不了。
阮如安幾不可察地眯了下眼。
——阮賀兩家的聯姻,果然不是表面上的單方面扶貧。
可當時的賀天賜也只是個剛繼承鍋碗瓢盆的畢業生,除了「名門之後」這個窮架子什麼都沒有,他又憑什麼值得阮父嫁女賠錢,扶持他上位呢?
而且阮父又怎麼放心讓『阮如安』這綿羊一樣的人嫁進賀家?不怕她壞事嗎?
無數猜測湧上心頭,但又在看到正廳的時候消散了。
兵來將擋,先看看阮父怎麼出招吧。
*
但阮如安沒想到,剛跨過正屋的門開,迎來的就是劈頭蓋臉的指責:
「阮如川,現在已經十二點零三分了!比約定的時間足足晚了三分鐘!你是怎麼安排的?為什麼讓你妹妹一個人在院子裡逛了這麼久?」
阮如安楞了一下,這才反應過來阮父是在罵便宜哥哥,便忍不住道:「爸爸,是我……」
「讓你說話了嗎?」阮父冷眼一覷,又把矛頭轉向了自己的兒子,「阮如川,說話。」
他的語氣並不憤怒,卻帶了一種不怒自威的感覺,令人忍不住自殘形愧。阮如安的心一時竟也漏跳了幾拍,心底不受控制地生出窘迫、茫然與愧疚。她下意識地張嘴想要解釋,卻在開口的剎那被人拉住了手指。
阮如川的嘴角朝她彎了幾個像素點,才低下頭對著父親致歉:「對不起爸爸,是我沒安排好人提前去接軟軟,耽誤您吃午飯了。」
阮父靜靜地睨了他片刻,才緩緩露出滿意的笑容:「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軟軟你也餓了吧?來,來爸爸身邊坐。」
緊張的氣氛瞬間和緩。阮如安抬頭看了眼自己的便宜哥哥,只見他眉眼低垂,神情冷漠,麻木得像一隻沒有靈魂的木偶。
阮如安忽然感到一陣窒息。
從始至終,阮父都沒對她說過一句重話,擺出一個冷臉。但她就是不由自主地感到愧疚和懼怕。
這一刻,阮父就像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將「偏愛」與「苛責」劃得涇渭分明,又分別賜予自己的一雙兒女。然而被偏愛的,只會在一次又一次的愧疚中蜷縮;被苛責的,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選擇沉默。
好一手封建大家長式的pua。
在這樣一捧一踩的教育方式下,也難怪阮家兄妹都脾氣隨和,沒什麼大的主見。
傭人為兄妹倆拉開紅木椅,等他們坐定,阮父才拍了拍手,示意上菜。
「爸……」
阮如安試探著開口,卻被阮父抬起一隻手打斷了:「食不言,寢不語。軟軟,你雖然是賀家的人了,但到底也是我阮家出去的女兒,要講規矩、懂禮儀。有什麼話,我們飯後再說。」
「是。」阮如安低頭受教。
餐桌禮儀在這裡得到了良好的貫徹。他們一家三口分別占據方桌的一邊,正與頭頂圓形的藻井湊成「天圓地方」的風水格局。兄妹倆只被允許去夾觸手可及的飯菜。閒聊當然也是絕對禁止的,餐桌上一時只能聽到瓷器碰撞的輕響。
在這樣壓抑的氛圍下,阮如安覺得端上來的珍饈都失了滋味,只期盼著這份折磨趕緊結束。
囫圇吞棗般地咽下了作為甜品的燕窩,阮如安朝著阮父投去目光,期待著這位前清遺老趕緊說話。
終於,阮父以清茶作為結尾,朝她開了口:「軟軟,你應該知道我為什麼要叫你回來。」
「是,爸爸。」阮如安垂下眼,乖順地聽著父親的訓話。
忽然,一道陰影籠罩了她,阮父溫熱的手落在她的肩頭:「軟軟,你是我捧在手心,連一句重話都捨不得說的女兒,你過得不好,爸爸的心也跟著一起泛痛,你明白嗎?」
肩膀上的熱意像一條粘膩的毒蛇,阮如安的心不受控制地砰砰跳了起來,方才胡亂塞下的飯菜一陣上涌,梗得她幾乎說不出話來,只能回了一個「嗯」字。
「爸爸也不是那種老封建,二十一世紀了,離婚也不是什麼大事。鄒家、沈家、王家……咱們豪門出來的閨女,就該比外面的野丫頭有底氣。」
「那我為什麼……?」
阮如安強行克制住本能的顫抖,坐在椅子上仰視著阮父,卻只能從他眼中看到不似作假的關懷。
「男人的事,你不需要知道太多,」阮父道,「你找誰當情人都沒關係,但多少要有些分寸。賀家早些年雖然是個空架子,但破船還有三斤釘,咱們阮家還有用得到的地方。」
他頓了頓,又說:「但我把你嫁過去,也不是讓你平白受委屈的。你再堅持一下,最晚到明年,我就同意你和賀天賜離婚,怎麼樣?」
小貼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1t;)
&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