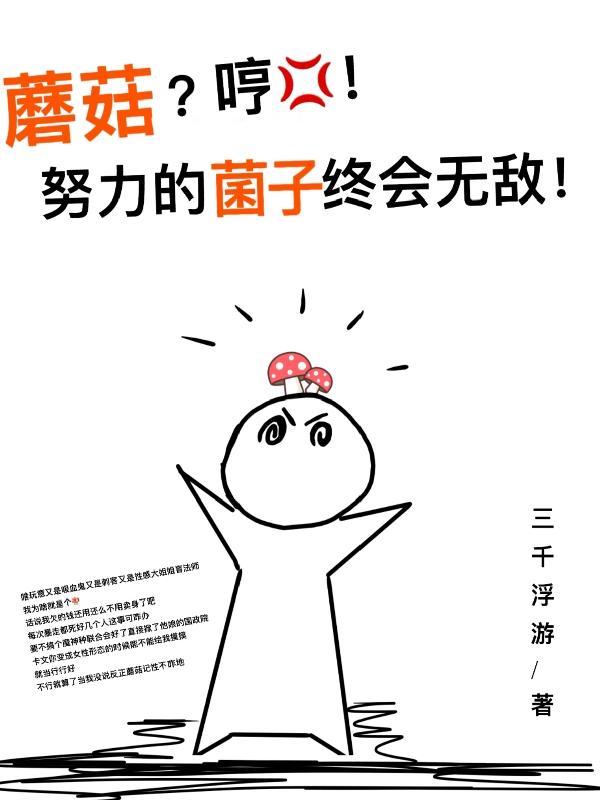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云水鱼图片 > 第102章(第2页)
第102章(第2页)
她工作相对忙,但只要在家,都会陪小虾到入睡。
床面下陷,应鸣生在她身后,替她揉着肩颈,“明天出差吗?”
“对,这次会去个几天吧,不出意外就能敲定,”
他是真学过按摩,向渔闭着眼享受,“过几天小虾满四岁,正好休假去庆祝下。”
“好,我们等你回来。”
按摩的力道变得不对劲,游走在锁骨,还有往下的趋势。但向渔还有桩事要说,止住他,而后转个面盘腿而坐,“你对小虾未来有很高的期许吗?”
应鸣生错愕了下,“没这么想,小虾平安快乐就好。”
向渔眯眼,怀疑地打量,“那你干嘛管小虾这么严,尤其是书面学习。”
小虾几乎是应鸣生一手带大的。
几个月大,夜里哄睡、冲奶、换尿不湿,全是他。会走路说话了,也是应鸣生带得多。
他是面冷心热的严父,小虾依赖且怵他。向渔和小虾则是朋友式的母女,一起玩一起闹。
小虾刚上幼儿园,应鸣生就选了各种早教课,日日不落地监督着。
该说不说,很像要培养个什么状元出来。
付出更多的人掌握话语权,但她也不能完全不管。刚接水路过,小虾磕磕绊绊地读着英语,脸都要皱成苦瓜了。
应鸣生默了一秒,“你学习很好,小虾是你的小孩。”
两人对彼此再熟悉不过,向渔顿悟——小虾是她的小孩,所以不要遗传他。
他读书不行,怕遗传给小虾,拖累她的好基因。
向渔一时语塞,不晓得说什么好。婚都结了这么多年,小孩都上学了,业内都是顶尖级别的纹身师了,他还认为是高攀了她。
她无奈地说,“那万一小虾遗传到我糟糕的艺术细胞了呢?火柴人简笔画都画不好的那种。”
应鸣生坚持,“像你就够了。”
怎么会有这种人,连她的缺点都可以视而不见。向渔叼住他的喉结,用牙齿磨了磨,引来一串意味不明的喘息。
惩罚完,她环着他的脖子,“卵子是很聪明的,它会筛选出最喜欢、最优质的去结合。也就是说,我的基因选择了你。”
“谢谢你。”
他诚挚得像忠臣受赏,表达一种“万分荣幸”
。无非是太过爱她,以至低到尘埃,常觉亏欠。
向渔手指抚摸着他的眉眼,蜿蜒着到唇,回应他:“我爱你。”
应鸣生低头,高挺的鼻梁与她的鼻尖缠绵在一起,舔了舔她的指尖,“去几天?”
“3天。”
他摸着向渔无名指上的戒指,好似在确认是否有戴着。
他总爱这么做。
“算上今晚,4次。”
湿热的吻印在耳后,细细密密地延伸。
窗帘翻飞,寒月洒到向渔半张脸上。她埋在枕头里,眼泪和发丝黏在一起。
不是说,男人过了25岁就走下坡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