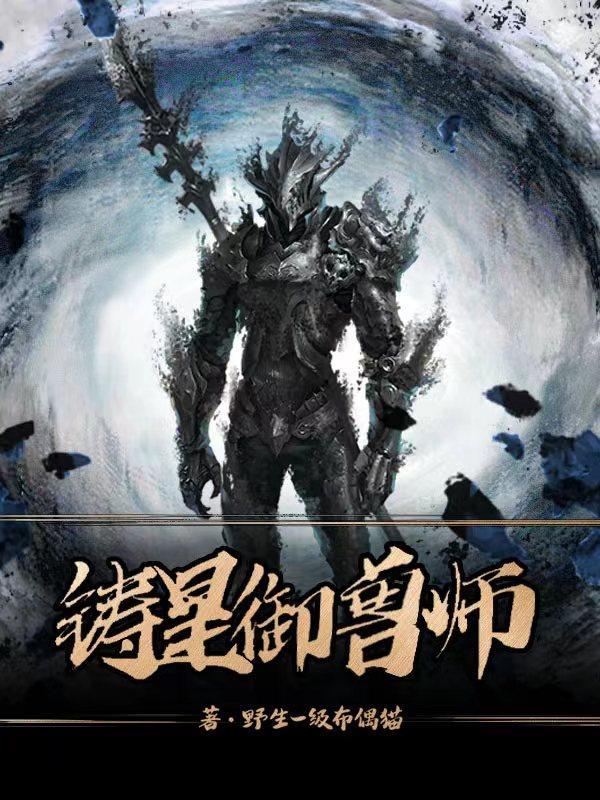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猎证法医6尘封卷宗番外 > 第18章(第1页)
第18章(第1页)
“那纯粹是罗家楠和陈飞他们自己作的。”
林冬抬手示意他不用尝试说服自己,“我翻,以谁的名义去翻?办案经费谁出?你总不能指望老贾花公款办私事。”
确实,唐喆学不得不认同。翻旧案,除非有明确的线索上来、取得上级主管的批准后才能开展工作,否则真不怪林冬残忍。不过贾迎春这人抠门归抠门,为人称得上光明磊落,而且也是干刑侦的出身,敏感度高,他要认为有问题,十有八九是真有问题。
彼此间沉默了一会,他听林冬感慨道:“老贾可能是心疼徒弟吧,毕竟才四十多岁,就这么走了……可是铁证如山啊,申诉十多年都没个结果,你知道么,邦臣到服刑完毕都没签认罪书。”
“也许……他真是被冤枉的?”
林冬没接话,只是转头看向车窗外。入狱的十个有九个喊冤,不能单靠个人感情来评判真伪。邦臣交待不出金劳力士的来源,表带上还有他的指纹,这案子搁谁判,他都是罪犯无疑。但是有一点疑惑,刚贾迎春提过,他也意识到了相同的问题——盗窃案最终没有完全侦破,除了那块金劳力士,其他的被盗物品无一追回。
如果不提邦臣,而是查整起失窃案,也许……想到这他赶紧闭了闭眼,打断惯性思维。其实他刚才看贾迎春说着说着眼眶都红了,确实心软了一瞬。可一想到之前查付立新儿子的案子给老付同志差点送进去的事,他赶紧暗暗掐了自己一把,强迫自己保持“不吃亏”
的人设。退一步讲,要是罗家楠或者祈铭找他,帮一把也就帮了,毕竟从他哥到他自己都欠人家两口子的情,至于其他人……
只能说,好人不好当啊。
林冬不接茬儿,唐喆学自然不好多说什么。他相信对方的决策,不管工作还是生活上,只要是林冬做的决定,他一向举双手双脚赞成。偶尔他会觉得自己过分依赖对方,也想过去当“拿主意”
的那个,然而事实证明,林冬真是吃过的盐比他吃过的饭还多,最优解永远在对方手中。
就像早晨指导胡景佑做暑假作业那事,林冬自有底气拆祈铭的台,搁他?一高考数学六十分的文科生,在祈铭那种顶级学霸跟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开了将近俩小时,两人抵达杨谢的工作单位。杨谢没继承老爹老妈的衣钵,不在营业室待着了,而是客户服务部。本人看着没照片上圆润,可能是年龄问题,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所致。眼睛看着不怎么聚光,不像是块难啃的骨头。
于会客室落座,林冬瞄了眼杨谢左手的无名指,发现留有戒圈的痕迹,但是没戴戒指,遂大胆做出判断:“你是准备离婚了么?”
杨谢正和唐喆学互相自我介绍,忽听林冬上来就查自己户口本,眼里不觉闪过丝惊讶:“啊……是,您怎么知道?”
“职业病,请别介意。”
林冬端起职业假笑——敲山震虎,直接让对方知道他的洞察力有多强,别想着编故事。
视线游移了片刻,杨谢谨慎地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林冬偏头示意唐喆学给他看叶蕙的照片,随即开门见山的:“你认不认识照片上的这名女性?”
看到照片,杨谢的视线定了一瞬,迟疑着摇摇头:“不……不认识……”
“确定?”
林冬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杨谢稍显局促的:“啊……也……就……好像有点眼熟?”
“我提醒你一下,钟田大学城。”
“噢噢噢噢,你这么一说……一说……”
杨谢抬手抓了抓脸侧,“她好像……是……是我爸他们……他们营业室的?”
回答问题时出现抓脸之类小动作,代表下意识的回避,怕答错而给思维一个缓冲的时间段。林冬确认他心虚了,继续发问:“在你就读明光学院期间,她被人杀害了,这件事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你一点都不记得了?”
“……”
喉结上下滚了几滚,杨谢稍稍侧过身,避免直视警官们的视线。余光注意到他正在揪西裤的布料,林冬当机立断穷追不舍:“她是你爸爸营业室的柜员,你爸爸在家里有没有提起过她?你妈妈知不知道她?”
“我妈跟她没关系!”
杨谢断然否认,说完意识到自己可能失言了,又磕磕巴巴地解释:“不是,我是说……我妈跟我爸不是一个营业室的,她不……不认识叶蕙……”
“叶蕙?”
林冬故作诧异状,“我从进来就没提过死者的名字,你刚不还说不认识?”
“——”
这下杨谢张口结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tbc
只看杨谢的反应,唐喆学基本断定这把没锁错人,叶蕙的死和鲁敏有关。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可知叶蕙死时被别有明光学院校徽的衣服蒙住了上身,作为明光学院的在读学生,那件衣服必然属于杨谢。现在要追的是,他是事后得知还是案发时就在现场。前者涉嫌包庇,后者则涉嫌故意杀人罪的从犯。
然而打从秃噜出叶蕙的名字,杨谢这嘴就像拿502胶水粘上了一样,闭得死紧。他懂法,没把自己提进公安局审讯,说明林冬他们手里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要咬死了不招,警方根本奈何他不得。
对付这号人,林冬可谓经验丰富:“既然杨先生没有什么要说的,那我们就不耽误您时间了,等下还要去走访您的父母,感谢配合。”
言罢起身,招呼唐喆学走人。出了银行大楼,他对唐喆学说:“赌二十块钱,他正在给他妈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