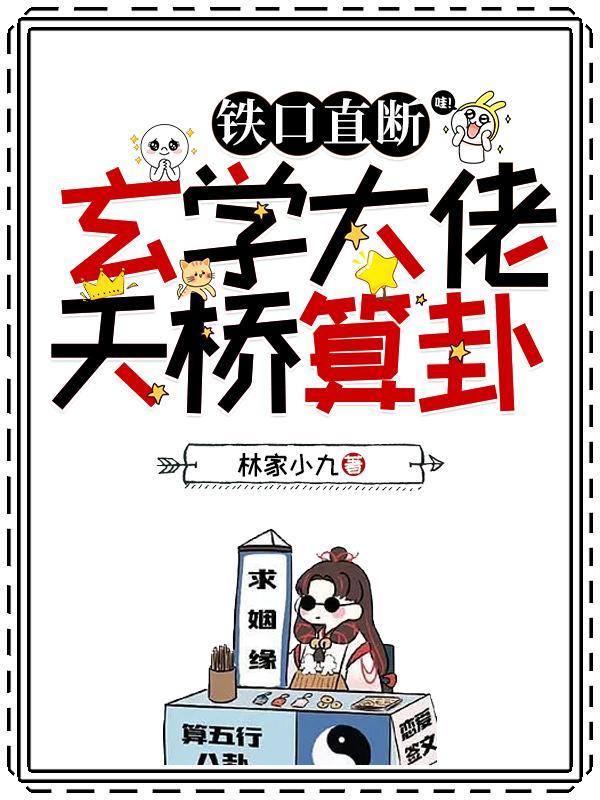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不请长缨是什么意思 > 第48章(第1页)
第48章(第1页)
郁濯接着道:“前几日我俩一块儿去了温泉庄子,左不过那晚他不尽兴,眼下才瞧着郁郁寡欢。”
“你既在这林子里躲着,想必听得很清楚了,他方才还因着我和二殿下的私交而吃醋呢。”
郁濯眼里含笑,问他,“你倒是说说看,这该怎么办?”
元星津心乱如麻,思绪万千间,他陡然抓着点话头,怒喝道:“不对!你方才分明说要讲一讲他的心上人!若真如你所说,你们感情和睦,你又何出此言?”
“他的心上人就是我。”
郁濯理直气壮道,“我俩婚前一南一北,成亲不过月余,他对我的过去如此好奇,本就不失为一种情趣。”
郁濯说完这一通鬼话,还嫌不够似的,他想了想,忽然偏头,薄唇擦过周鹤鸣颈侧,直直滑过到他柔软耳垂,方才餍食一般离开了。
周鹤鸣猛地怔愣在原地。
其实那唇划擦的速度极快,蜻蜓点水一般地过去,带着点温热的吐息,可偏偏剎那阻断了林中风雪,奇异的麻劲儿沿着周鹤鸣的背脊,一路飞速窜上来。
他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郁濯做完这一遭,挑衅般睨着元星津,幸灾乐祸道:“还要继续问吗?”
“郁二!”
元星津羞愤交加,因着方才那个撩过侧颈绵延至耳垂的吻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听着身体本能咬牙切齿地朝郁濯追去,叫唤道,“我杀了你——”
他穷追不舍,郁濯便绕着周鹤鸣躲,二人隔着周鹤鸣秦王绕柱,混乱之中雪泥飞溅,周鹤鸣方才从刚刚猝然的亲密里回过神来。
他耳根不知何时已经红透,这一场闹剧实在忍无可忍,他拽着郁濯的手腕将人拉住,生生将二人隔开,语气古怪道:“够了。”
“你偏袒他!”
元星津只觉心如死灰,他伤口已经不再渗血,干涸的血迹被寒风吹得斜飞在脸上,配着点殷红的眼尾,瞧着实在可怜。
元星津喉头哽塞道:“三年前你还亲自带着我在莫格河滩上跑马,在白鼎山中打猎,我的箭术都是你教的。你说青州永远是元家人的故乡,我随时可以回去。”
“现在也一样。”
周鹤鸣一向将元星津当弟弟看,从来没见他这样过,皱着眉尽量安抚道,“你回来,我还带你跑马打猎。”
“是啊,”
郁濯从周鹤鸣身后探出半个脑袋,说,“我也带小世子一块玩儿。”
周鹤鸣喟叹一声:“你别说了。”
郁濯带着游刃有余的笑,他此刻又重新变作了狐貍,身上系着的那件氅衣毛绒绒的领子也好似变成了故意露出的尾巴,这尾巴被林间风吹散了,丝丝缕缕地往人心里钻。
痒。
这痒简直无孔不入。
周鹤鸣发誓自己并无任何刻意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