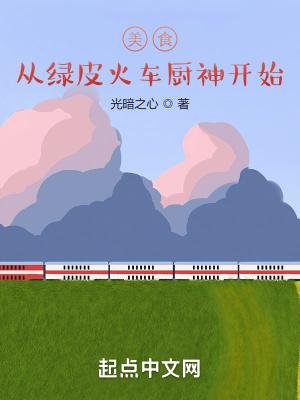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港岛风月片无删减版 > 第四十四章 我很喜欢你的礼物(第1页)
第四十四章 我很喜欢你的礼物(第1页)
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余幼笙从卧房浴室出来,见季宴礼又在厨房忙碌。
男人同样刚洗过澡,湿软发梢滴答落水,渗入浅灰色的家居服,颀长背影肩宽腰窄。
灶台上小锅里正炖煮着剪碎的银耳、枸杞、以及去核红枣,远远便能闻见清淡香气。
听见她脚步声,季宴礼关掉小火,用漏勺捞出含有糖分的红枣和枸杞,将剩下银耳汤倒入饮杯。
热气袅袅飘升,却不见男人眼镜起雾;余幼笙在餐桌边坐下,还沉浸在刚才的尴尬中。
她轻咳一声,开启话题:“你是近视吗。”
睡前她偶尔见过季宴礼不戴眼镜、人靠在床头处理工作,阅读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季宴礼最后在饮品中加入奶粉,手背确认温度不烫后,放在余幼笙手边:“镜片会给我掩饰情绪的心理安慰。”
绝口不提半小时前的窘境,男人朝她微微一笑:“生意场上,情绪太外露,很容易被人抓到弱点。”
余幼笙似懂非懂地点头,低头喝丈夫每天换着花样准备的睡前饮品,舌尖满是浓郁奶香,感叹连连。
她慢吞吞喝完整杯,抬手将杯子递过去时,季宴礼忽地道:“今晚你先睡吧,我在书房处理些工作。”
“好,”
余幼笙点头理解他忙,轻声叮嘱,“我给你留门,你也早点休息。”
女人刚洗过澡,眼尾都漾着点点殷红的模样看的人细软。
季宴礼将杯子洗净,擦干手后轻揉余幼笙发顶,柔声:“一个人睡怕黑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不满对方拿自己当小孩,余幼笙轻声反驳:“我都多大人了,怎么会怕黑。”
“那就是我以己度人,”
和她说话时,季宴礼总会习惯性地俯身平视,半调侃的温柔语气,“是我一个人怕黑,晚上找你来睡觉可以么。”
搬来当晚两人就同被窝睡觉,余幼笙被问只觉得莫名;即便如此她仍微偏着头,认真思考几秒,提出方案:
“明天周日不上班,你怕黑的话,我可以在旁边开灯陪你工作。”
“……”
话落那时,她仿佛透过镜片,在男人眼底见到太多翻涌情绪,有一瞬甚至错以为,自己是早被盯准捉捕的羊羔。
然而,季宴礼最终只勾唇笑了笑,送余幼笙回床上躺下、掖好被角后,委婉谢绝好意:
“快睡吧,不舍得拖累你。”
余幼笙当晚睡的并不太好。
许是睡前男人随口一句逗趣,又或许这是同居后余幼笙第一次独自睡,晚上她躺在空荡柔软的大床时,难得失眠。
鼻尖不再是熟悉的涩苦木质冷香,她侧身睁眼,被窝里微蜷着身体,没人捂热的手脚微微发凉。
习惯是件太恐怖的事,平日不觉得,非要跳出舒适圈才自知其中冷暖。
睡前护肤时,她无意从半开房门中,见到季宴礼似乎拿着什么,走进那间专用于办公、平日不便让她和王阿姨进去的书房。
这是余幼笙第一次见男人进那间书房,屋内并未开灯,向里看也漆黑一团。
让只身走进的季宴礼,仿佛踏入无尽黑暗。
自知深夜乱想太荒唐,余幼笙辗转反侧毫无睡意,几次想起身找季宴礼、又怕打扰他工作,最后决定给男人发消息询问,问她方不方便过去。
季宴礼那晚应当真的很忙,从来收到消息都秒回的人,在余幼笙昏昏睡去前,没有再回复一个字。
第二日清晨,余幼笙被卧室外面传来的菜香勾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