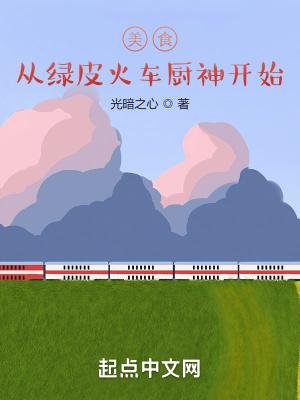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貌美万人嫌总被窥伺(快穿) >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第1页)
李砚辞见李悼抬手想要去抓他的衣襟,皱着眉躲了过去,眸光又冷沉了几分,寒声道:“来人,堵住这个疯子的嘴,把他给朕压到迦叶床边去。”
让许迦叶看一看李悼的脸,效果也是一样。
李砚辞话音刚落,李悼的拳头已照着他的脸砸了过来。
李砚辞一身的伤,行动不似往日那般灵敏,但李悼的虚弱程度不在他之下,这一拳倒是被他勉强格挡住了。
刘采连忙带着宫人们上前想把李悼控制住,却听见李砚辞冷声道:“不要过来。”
他想亲手打死李悼已经很久了。
“慢些捅,小心伤着手。”
薛柏清见二人把寝殿变成了战场,拳拳到肉、残血横飞,一副恨不得立时把对方就地格杀的样子,不由眉头轻蹙。
本朝连文臣都武德充沛,上早朝的时候一句话不合便有可能打起来,太宗年间,更是有文臣在乱战中被活活打死,但皇帝和王爷赤手空拳打起来,古往今来都闻所未闻。
倒是用上刀剑啊。
打到最后,李砚辞身上的伤口尽数迸裂,鲜血将新换的衣裳染红了。
刘采抱着视死如归的心命宫人上前把两人拉开了,让宫人们把李悼押在了地上,胆战心惊地跪下求李砚辞宽恕他的忤逆之罪。
陛下这又是发什么疯?若是实在是恨景王,有无数种法子解恨,何苦自己亲自动手。
动手也就罢了,还没赢。
李砚辞没有给刘采哪怕一个眼神,他走到李悼面前,脸色阴沉到极点,居高临下地道:
“朕等着你毫无价值、失去倚仗的那一天,到时候落在你身上的不会只是拳头。给朕滚到她床边去,如果她清醒不过来,朕就在这里活剐了你,她总会醒来看一眼的。”
李悼甩开了宫人们的手,定定看了李砚辞一眼,一瘸一拐地走到了床前。
他看向端坐于床榻上的薛伯清:“薛阁老在这里做什么?怎么,咱们这位陛下的疑心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要把全天下的人都怀疑一遍。可见他心底里也是清楚的,无论迦叶爱谁,哪怕是爱猫、狗、雀儿,都永远不可能会爱他。”
“我已经不是首辅了,殿下不知道吗?”
薛柏清别有深意地道。
李悼知道许迦叶养了山雀,又怎会不知他被革职下狱了。
李悼和李砚辞不愧是亲兄弟,为了放生山雀一事,一个迁怒许迦叶身边伺候的人,一个疯起来连皇帝都敢打。
李悼蹙眉,他在狱中仍能与外界有联络,但确实不知道此事,想来应该才发生不久。
现在不是关注这个的时候,他轻声道:“你知道迦叶她没了……”
没了孩子吗?
薛柏清想到方才李悼激愤之下的话,点了点头:“我劝过她,我想着要是有了感情却没留住,她恐怕会伤心至极,那时她叫我别多管闲事,没想到她竟……”
真的把那只山雀放生了。
他看向躺在床上的许迦叶,目光极其复杂,他劝许迦叶把雀儿放走是顾及她的心情,那她自己呢?她是打心底里希望那只雀儿能自由啊。
为此甚至不惜自己难过。
李悼暗叹了一声,薛柏清居然之前就知道了吗?许迦叶待他果真是不同的。
他指了指在床上蹦来蹦去的山雀:“这是什么,她既病着,怎么还弄这么一只吵闹的雀儿来打搅她。”
薛柏清声音极轻:“这是陛下找来的替代品。”
李悼愣了半晌,继而冷笑了一声:“我看他是得了失心疯了。”
他但凡找个孩子过来,不拘多大的,都能勉强算得上正常,搞来一只鸟骗许迦叶这是她的宝宝,她怎么可能相信,难道要跟她说这是她的孩子重新投了胎吗?
可见李砚辞是半点心都不用,只是随意敷衍一下罢了。
可怜迦叶……
李悼长叹了一声,对薛柏清道:“请让一让,我和她说说话。”
薛柏清微一颔首,起身站在了一旁,目光仍不离床上的人。
李悼坐到了薛柏清原来的位置上,终于瞧见了许迦叶的眼神,空洞、呆滞、没有半点儿神采,他只觉喉间骤然涌起一股腥甜之气。
若他那一箭没有射偏该多好?
白色的小山雀见又换了一个新的人,睁着黑豆一般的小眼睛看着李悼,拖着长长的黑色尾羽往他这里蹦哒了几下,叫了好几声。
李悼见它这么闹腾,心中厌烦极了,随手把它往旁边拨了一下,小山雀一个没站稳,差点倒在了床上,哀哀地叫了一声。
始终一动不动的许迦叶终于有了反应,她伸出了胳膊,看上去像是想把小山雀扶起来,声音轻柔:“宝宝。”
李悼只觉得自己的魂魄仿佛在剎那间被抽走了,留在这里的只剩下一副躯壳,与其说是心痛,不如说是迷茫,他是谁?他在哪?他还活着吗?
原来她真的分不清啊。
深不见底的悲哀霎时间将他整个人都吞没了,他咳嗽了一声,一行血迹顺着嘴角蜿蜒而下。
李砚辞快步走到床边,屏住了呼吸,把山雀捧了起来,轻轻放到了许迦叶怀里。
他紧紧注视着许迦叶,见她把山雀往怀里拢了拢,他扫了一眼坐在床上的李悼,第一次觉得他也有顺眼的时候:“你若是能让她清醒过来,朕免你一死。”
李悼面无表情,看向李砚辞的眼神中什么都没有,没有怒意、没有恨,唯余一片死寂。
“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救不了她,这是李乐衍死而复生都未必能做到的事。我的母亲去得早,但你承太后顾复之恩,又为何会不明白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舐犊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