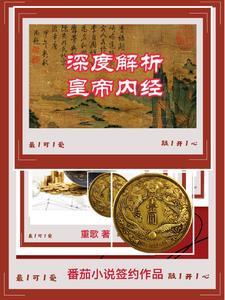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入高门民国 > 第十三章深夜里突然而置的男人(第1页)
第十三章深夜里突然而置的男人(第1页)
惠莲把脸上最后一层搽脸油抹匀,刚准备睡觉,盖被的手抬到一半,打外面进来个人。那人步子迈得大,身上混杂的脂粉味,随着布满整个房间。惠莲熏得掩住鼻,别过脸,表情是不加修饰的嫌弃,来人却跟没看见似的,也不上床,只坐在椅子上。“怎么这会儿过来了?”
惠莲问。他们结婚30多年,用脚后跟想都知道他刚从哪出来,没直接睡外边,怎么还跑她这来了,弄这么一股子死味儿!丁老爷大模大样坐在桌边,抖着褂摆,翘起二郎腿,跟她打听起丁伯嘉最近的生意。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出息,当爹的反而怵他了,知道了最近这段日子,惠莲和丁伯嘉忙活着盘账,丁老爷不敢往大儿子身边凑,只能到妻子这来摆谱。惠莲当即就明白,他在打什么算盘珠子,无非就是想拿钱,养着外头的那堆。她嘴角暗自一抿,看向他的眼里露出轻蔑的鄙夷,将身旁的被盖在身上,一副油盐不进的态度。三言两语就打发过去,以前也就算了,他赚钱想给谁她也说不得什么,现在想拿她儿子赚的养外面小的,门都没有,府里一大家子人哪个不用花钱!空气中一片寂寞,夫妻之间如今只剩下疲惫,多一句话也不愿与对方说,惠莲作为正室,心里只有主母的责任。相顾无言,惠莲躺了下去,没做出给他留位置的动作,一张大床占据正中,丁老爷跌了份,不愿在这儿多待。临走前,忽然想起自己新进门的小老婆,回身随口一问:“五太太最近怎么样?”
惠莲心头莫名一紧,思索着把他打发出去:“挺好的。”
眼尾朝他一瞥,稀松平常接着道:“太晚了,大家都睡了,别去打扰别人了。”
丁老爷听出来,这是不想他过去,细细回想了下谢菱君,只记得长得美,可美的人多得是,且性子又太傲,他没那耐心捧着她。琢磨一番,也没了打算,他只要她泡过的药丸就够了,才不上赶着贴冷脸。惠莲得着他又出府的消息后,踏实闭上眼,长长舒了口气,一觉睡到天亮。夜里,灯儿睡得浅,院门轻轻扣了两下,她快步过去打开门销,门外站着意想不到的人。她怔怔立在那,满眼错愕,还没来得及出声,那人就将手指竖在唇中,轻轻一嘘,接着径直越过她,直奔正房而去。灯儿看着那人背影,身上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带着微湿的水汽,像是从别处紧赶回来的。只是,怎么回来就直奔这儿了?屋内光线昏暗,来人却长了双鹰眼,精准朝着床边去,脚下步履轻快,一看就是有童子功在身,这么高大的身材,落地毫无声响。
男人的眼直勾勾盯着女人的睡颜,随之往下,腰间衣摆被蹭了上去,露出一截雪白的腰肢,他沉沉望着,默默滚了下喉结。他听说她病了很久,心下着急,却也只抽出这么点时间回来,只为看她一眼。情不自禁伸出的手,悬在空中,顿了顿,最后把衣服拉下来,屈起食指,在脸颊上轻轻揩动了两下。指腹下的滑嫩,一如他所想象那般,像块鲜嫩豆腐。黑暗中,男人冷峻的眉眼,霎时柔和下来,眉眼间漫上丝丝情意,可不知又想起什么,一股和气质相符的冷冽,压盖过温情。谢菱君在枕头上蹭了蹭,把薄被往肩头拉了拉,发出一声微弱的哼唧。男人无声笑了下,轻声吟语:“小猫似的。”
边说边把盖在嘴边的薄被,掖到脖子下面,便没再没有多余的举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门外传来细微的提醒:“该走了。”
男人周身的气质恢复原样,对着床上的身影最后说了句:“等我回来。”
走出正房后,灯儿还在院中等着,他看着小丫鬟,露出些许满意的表情,是个安分衷心的,这样的人放在谢菱君身边,他才放心。整个丁府,灯儿最怕的就是眼前的男人,他不同于其他人,身上带着肃杀之气,压得人抬不起头。男人清冷干脆的嗓音,在她头顶道:“你是老大的人,还是老三的人?”
“都、都不是…我是五太太的人。”
灯儿打着颤,如实回答。但灯儿心里也明白,男人这么问,就说明谢菱君的一举一动,他都清楚,甚至是刻意盯着她,灯儿头皮发麻,只觉贴身丫鬟原来这么难做。高大的男人似是看穿她的想法,眼尾睨着她轻哼着:“记住你的话,不要做出任何背叛她的事,你以后的日子不会差。”
语毕,他半侧身,朝着亲信示意,亲信从内兜掏出一枚铜牌,递到她手上。铜牌上面刻着字,灯儿自然知道这是什么,不明所以大着胆看了他一眼,男人告诉她。“有任何事,拿着它去找我,有关你们太太的,不论大小都可以。”
“记、记住了。”
灯儿忙把它收好,看着男人踏着月色悄无声息的来,又匆匆离开,黑色的身影隐在黑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