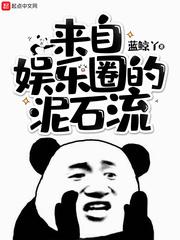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殿下追妻火葬场啃菠萝的猫 > 第83頁(第1页)
第83頁(第1页)
直到最後一樣,沈驚墨的拳頭已經緊緊攥在一起,發出「咯吱」聲響。
箱子裡面有一卷紅艷的婚庚,洗淨的白繃帶,有他贈予沈歧的玉佩,交給沈歧調遣濟善祠的令牌,借給沈歧穿的衣裳,特意為沈歧打造的面具,一些平日裡送給沈歧的小玩意……
這些,多多少少是他和沈歧相處的證明。
亦是,宋歧欺騙他的證據。
彼時宋歧還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身後微不可察的聲響驚擾了他,他側眸看去,地上不知何時多了一件披風。
順著向上,是少年陰沉的面容,溫潤多情的桃花眸徒留一片冷意。
「墨、」
啪——!出手凌厲迅猛的掌風快到捕捉不到殘影,落在宋歧臉上發出清脆聲響。
宋歧的身子向一側偏去,手中木箱重重摔在地上,裡面的東西撒落一地,神情是肉眼可見的慌亂。
越是著急,重心越是不穩,宋歧踉蹌著向後退了好幾步,雙手扶住身後棺槨,咽下喉間湧上來的腥甜。
他有些無措地看著地上的散物,又有些彷徨地看看沈驚墨。
「你讓我感到噁心。」
沈驚墨語氣森寒,聲音低沉而嘶啞,在宋歧的注視下,一字一句,決絕離開。
宋歧的臉色已經再無血色可言,他想追上去,猝不及防一口鮮血噴涌而出,身子不堪重負撲跪在地上。
沈驚墨一怒之下離開了歧王府,疾在街上穿行,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遠離歧王府。
不知過去多久,天色漸亮,日頭初升,街頭巷尾儘是販夫走卒,隨著時間的推移,吆喝聲越來越多。
沈驚墨漫無目的地遊走,來到了將軍府門前。
當初從將軍府獸場死裡逃生,醒來就在歧王府,蘭花道將軍府被大火蠶食乾淨,需要重修葺,而他因為某些羈絆不得不沿著上一世的軌跡生活,無法離開歧王府。
現在再看,將軍府被燒毀也是他們的謊言之一。
沈驚墨緩緩走過將軍府的每一處,明明都是熟悉到閉著眼睛都能找得到路的地方,卻處處透露著陌生。
他望著前院裡曾屬於他的鞦韆,娘親常常在後面推動他,時而騰起,時而緩落,一大一小,對著詩文。
沈驚墨目光移向前廳,陳年的記憶大多數都已經模糊了,許多東西也未曾記住。
只知父親大人威嚴,經常在此訓罰哥哥們。
尤記得兩位兄長借著踏春的名義帶他上後山獵野雞,摘野果,回來三個泥娃娃遭父親大人訓斥。
兄長們將他護在身後,哪知爹爹才捨不得責罰他,一把將他抱起,要為他洗去身上泥污,又怕自己手糙,喚來沈夫人給他沐浴。
沈夫人也是將門之後,推來推去,還是奶娘替他擦洗身子,全程兩位大將軍在一旁專心學習手法。
小驚墨才不懂他們緊張什麼,揪著肅有冷麵戰神稱號的沈將軍的臉讓他原諒哥哥們,沈將軍笑著連連道好……
冷風吹斷思緒,沈驚墨恍然明白,早在多年前,早在這些事不會再次發生後,將軍府就已經不是他想的那個家了。
沈驚墨開始收拾起東西來,倏然發現,沈氏沈宣嬌一家子的東西早已被丟棄,府上的奴僕,管家也已經全部換了的。
他在前面走,他們在後面,隔著一段距離規規矩矩跟行。
知沈驚墨有話要問,管家十分有眼力見的上前解釋:「奴陳廣白,之前在宮中御前做事,奉三殿下調遣,前來打理將軍府事宜,從今往後,只聽命於沈公子。」
陳管家招呼奴僕拿來一沓奴契,介紹人員布置,將軍府哪些地方進行過修葺,花費了多少銀兩,不過都記在了歧王府帳上。
他們甚至嚴查過將軍府之前的帳,從趕走的那些奴僕身上,要回來了他們貪污的銀兩珠寶,最後把那些人全部送進了大牢。
一切事宜井井有條,沈驚墨想做的,未做的,全部已經完美做完了,這一切,都是宋歧在背後打理。
沈驚墨說不出什麼感受,也不想去想那些糟心的事,草草打發了他們,獨自到寢殿休息。
前一晚才做了噩夢回想起那些不堪的過往,今天又回將軍府,給他帶來不少不美好回憶的地方,沈驚墨其實還不敢睡。
一閉眼,滿腦子都是那些被他刻意遺忘的過去。
可是不睡,後頸放射的疼痛牽連後腦,疼得他渾身難受。
沈驚墨側躺在床上,輕輕捶著後腦,實在難受極了,則會加重力道重重砸在床板上。
持續了一個時辰左右,好不容易熬來困意,門外忽然傳來窸窸窣窣的動靜。
沈驚墨淡淡瞥了一眼,收回目光,他真的好累,不想去管。
沒過多久,幾道人影不停地在門前徘徊,有人試著想敲門,嘆了口氣,放下了,反反覆覆,終是沒人敢推開。
聽他們交談,像是蘭花和昨夜給他看診的御醫。
沈驚墨輾轉反側,抵不住內心煎熬,起身快整理儀容,打開了門。
他沒出聲,臉色不是很好,便沒人敢先開口。
沉默良久,還是陳管家率先打破僵局,「沈公子,這些是歧王府派來保護您安全的,還有他們倆」
陳管家指了指周圍站崗的侍衛,又看向蘭花和御醫,「三殿下突然失蹤了,他們來這問問三殿下有沒有來找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