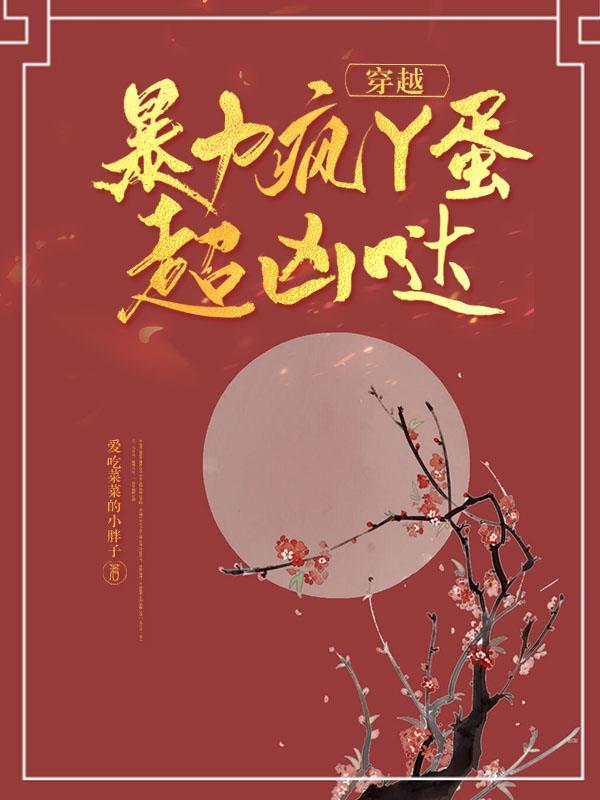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明我长相忆 > 第2章(第1页)
第2章(第1页)
疾驰过半个神都回到宫门口,即便是在深秋的早晨,额上也微微沁出一点薄汗。辛时从马背上跳下,一手还握着缰绳,另一手已经拉开腰上小袋,将出入宫门的符牌用两指一夹,抽出递给城门守卫查看。
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丝毫多余。城门郎见他急切,忍不住打趣道:“辛待诏一大清早入宫面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儿的大将军打了胜仗,怀揣捷报。”
得人调侃,辛时却也不恼,只回笑道:“确实是捷报。”
说罢收起符牌,穿过宫门又翻身上马,抄进夹道往翰林属院奔去。他走得急,因而未听见道旁两个持帚的宫人轻声絮语,正是在念诵一首诗: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走马入宫门……”
辛时回到翰林院的时候,门口刻漏壶中的羽标刚刚浮起,是一日伊始时才撤换过的水面。同僚们皆未应卯,只有零星几个宫人在添灯补墨,见他踏入门内,纷纷行礼。
辛时脚步一拐,拐入院墙上开着的小门之中。
小门内绿意尚浓,不同于中央神道上的枯叶梧桐,到处可见生机。辛时径直走上院内小楼二层,边走边宽衣解带,将沾染了跑马灰尘的外衣脱下,站到窗前洗手净面。他换一套新的袍服穿上,系好腰带之后顿一顿,最终还是走到墙边的高柜前翻出一盒香丸,取一粒压在舌下。
做完这一切,神清气爽。
天色终于见亮,一轮旭日半沉在天边,雄圆浑厚。辛时步行在宫道上,呼吸间皆是水雾的清冽,约一刻钟后走到含宸殿外,登上台基,站定,不动。
含宸殿是天子起居之所,此时殿外两列宫官排着长长的队伍,手捧食盒,显然是逢殿内那一对夫妻的用饭时刻。与同僚们不同,辛时并没有固定的当值时间,非要说的话便是有事即来、事毕再走,比如说遇到昨晚这样的特殊情况,就得大半夜爬起来督促武侯们抓刺客,在天子夫妇起床前料定一切,等着第一时间彙报消息。
高大的廊柱下有人影晃动。辛时定睛去看,认出是皇后应氏身边随侍的女官吴氏。吴氏显然也看到了他,远远地一顿,向他轻轻颔首,随后转身步入御内,留一抹裙锯曳地,款款微摇。
即便女官入内通报,辛时却知道等两位圣主真正召见他还要不少时间。他几乎能想象出殿内夫妻的对话,神皇听见他来,一定会立刻放下筷箸,而神后也一定会将性急的丈夫安抚,说诸如“陛下莫急,待朝食之后再理朝政不急”
之类的话。
自从七年前北海一役,天子圣体频频欠安,于国事日感无力。皇后辅政,二圣临朝,已经不是什麽稀罕事了……
辛时望着朝阳下含宸殿熠熠生辉的瓦面,逐渐发起了呆。
二十多年前,前朝暴君无道,天下大乱。各地人马揭竿而起,大小军阀混战不休,寇贼四起,生灵涂炭。最终是河北王杨暨与其王妃应氏感念民生艰辛,东征西讨统定江山,建立新朝为周。
对。如今的天子,可是大周的开国皇帝呢。无论在朝在野,都极有威望。
定国号为周,是向先周文王武王天下大治的盛世看齐的意思。自从杨氏大周开国后,天子励精图治、修生养民,因此五年后长安周围八水齐现白玉神兽,是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祥瑞。天子大悦,将年号从原先的“天始”
改至“昭德”
,沿用至今。改过年号的第二年,天子夫妇始加称号为“开国大尧皇帝”
与“开国大母皇后”
,八年前又上尊号为“开国大神圣尧皇帝”
与“开国大圣神母皇后”
,并称“二圣”
,也就是如今大家都习惯简呼的神皇与神后,而国都长安也自此改名,称作“神都”
。
当然,这些事情都并非辛时亲眼所见,而是在帝王实录上看到的。他的年纪甚至还没有新兴的大周王朝来得大,到天子夫妇身边供职也是只四年前的事情,那时候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不知不觉,已经四年了啊……
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幽幽的声音。
“辛待诏久等。陛下已盼多时,请你入殿。”
辛时眨眨眼,轻轻“啊”
了一声,游走天外的神思被拉回眼前。
天色已然大亮,连鸟鸣也喧嚣了几分,奉食宫人们不知何时已经撤下,殿门外空空蕩蕩。天子夫妇终于準备好要见他,辛时向传旨的宫人道声谢,拾着台阶而上,才走几步,猛地又想起一件事——
他今天不知怎的感怀旧事,发呆发太久,忘了筹措面圣时的言辞。
只一瞬间,辛时就把“我没有準备好面见二主时该说什麽”
的忧虑抛回脑后。
面圣嘛……一回生二回熟。辛时早不是第一次面圣会被天子威仪吓到失色的无名小吏,一天指不定要在御前跑上几趟,既然忘了準备,那就……有什麽说什麽呗。
一进入含宸殿,光线立刻暗了下来。
这只能怪殿内结构过于高大。二层假檐,进深宽广,即便三面有窗,能够透过长廊照射进来的光线也称得上有限。更何况现在只是朝阳初起的清晨,灯台上只点着几盏灯火,屈指可数,幽幽寥寥。
这倒不是为了节省开支。无论如何,杨氏天子身负改元易色的丰功伟业,总不至于省几个灯油钱。天子夫妇在用度上算不得奢侈,但也绝不节俭,会将殿内拾掇成这般,还是因为天子的身体状况。
神皇近些年在医药方面愈来愈依赖于内庭道宫的术士,晨起时不宜强光,便是遵循他们的医嘱。不仅如此,天子盘腿而坐的御床前还坠着数层淡绿色的长纱,这也是道宫术士的提议,因时值“朝阳初升,昼夜交易,阴阳不稳”
之际,邪气易入,不宜直接面见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