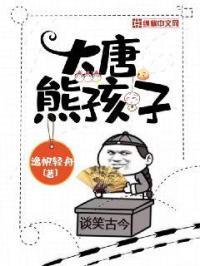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明日无界 > 四十五意外(第3页)
四十五意外(第3页)
短暂的沉默后,所有男人都止住汗,鼓足劲跟他喊,声音愈齐整、愈高昂:“不、不配!不配呀!不配!不配!不配!”
他们喊了许久,久到桑登的心不再乱跳,而是一顿一顿,敲出强有力的音,在胸中震荡,让失控的身体暖、热,热到情愿流汗更自愿洒血。
“说够了?”
阿竹背负双手逐一审视这十七人,讲出流畅且威严的特罗伦语,“我曾讲过,你们这种蠢货就该绑好石头跳进海里,怎敢游出来惹事?”
“去你妈的疯狗!”
领头的壮汉骂完便笑,嘴角几乎张裂,“惹事?是杀你们这些背叛者和异种来取乐!可惜遇上你这贱种,没能如愿而已!来吧,杀了我们吧!但你记住,特罗伦人没有孬种!总会有人挺身而出,让你们这些背叛者和异种都永不安宁!你等着吧!会有那天!终会有你这盗用帝皇之名者不能阻拦的一天!”
听见这声音的桑登想哭,却流不出泪、握不紧拳,跪倒的身体虽站不起,心里仍默念着相同的信念。或许广场上的特罗伦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相信迟早会的,是的,迟早会的…
那救赎的一天定会来临的。
“杀人取乐?你是认真的?”
作为回应,阿竹用五指握紧了自己的脖自,生生将自己的头连着脊椎拔出,用脊椎当鞭子,抽歪了壮汉惊愕的脸,而后复原躯体,继续大笑,不过是那种肆意的嘲笑,“看见了?世间罕有的蠢货?试问,面对当生死亦可逆转的我,你的取乐又能有什么意义?”
好半天才回过神的壮汉猛咳一口痰,向他吐出了浓黄的黏液,以表心迹:“呸!妈的!要杀就杀!别拿你这疯狗的血玷污圣环广场!”
可痰液硬生生溜回壮汉的嘴。壮汉本欲再吐,腹中却猛生收缩的响,令一种空虚传至脑中,让涎水狂流的同时忍不住卷起舌头,嘴不由一吞、喉咙再一咽,将恶心的玩意吞下肚,连连作呕:“妈、妈的!怎——”
“吵闹且恶心的蠢货,我会给你与那口‘美食’相符的惩罚,”
阿竹收起笑容,疤与嘴有些微微地挑动,“与我领悟的道理相符的惩罚。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会给你们永恒的生命去饱尝折磨,说你们最后的感想、嗯,是叫忏悔,对吗?”
壮汉竭力忍耐不知从何而来的饥饿感,鼓足力气叫骂:“永恒?最后?忏悔?他妈的疯狗!最后我会操你的妈!跟着再好好忏悔!我——”
辱骂刚结束,凄厉的惨叫便爆。而在这痛苦的嘶吼中,桑登看见七人的肋骨带着血钻出胸腰,骨骼更从手腿里飞出,而后他们的臂贴着身体粘连,两腿则绞在一起愈合成尖长的尾。最终,这些人重生为十七条人面肉蛆直飞高空,射往圣都的不同方位,带着咒骂渐渐远去。而阿竹则叉腰肯,瞟过他在内的跪地者,消失不见:“今日我就宽恕你们,滚吧。”
桑登瞬间起身,挤出同样重获活动能力的人群,拼命跑出广场,踏上一道金色直路,追赶不知飞往何处的壮汉。
桑登一直跑,跑了很久、很久,直到听见些古怪的声音才刹停,更听出声音是从前方、不,地下传来,便急忙以耳贴地,果然听得更明白,觉得那像是夹杂吞食的辱骂声,又起身继续跑。声音越来越响,响到桑登揭开井盖爬进下水道,掏火机照亮护栏下方的黑色浆液,忍着反胃感搜寻声源。
没等桑登细看,一条黑臭的东西猛地撞来,在挂住护栏后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桑登小心靠近,在抖动的火影中见到一张滴落污浊的嘴正咬死护栏的铁杆,遮满黑脏流体的眼只是眨。桑登顾不得脏臭,抹净那张脸,果然是壮汉的容貌——
“你?!杀了我!你!杀了我!”
看清他后,那东西欣喜声,却又坠落,只能像条蛆一般在这脏臭的地狱蠕行吃食,永无止境、永无止境。
已不用多看,桑登翻过护栏跃下,一脚跺烂尚存人形的头颅,给其解脱。可没等桑登喘气定神,那抽动的烂肉已完整重生,看来使者赐予的“永恒”
并非妄言。
复活的人蛆一口咬来,险些啃住桑登的腿,逼得他跃回安全地,撑着护栏俯视蠕动长条上黑的脸。他的手越攥越紧,捏得栏杆嘎吱响。他打算再翻跃而下,双臂却撑着身体一步步退后。这本想给同胞解脱的男人终是默默爬出下水道,更把井盖归位,在人面巨蛆那混杂吞食、呕吐的嚎叫中趔趄躲开。
求饶了,人蛆求饶了,不是向朝晟的疯狗求饶,而是向尊敬班布先生、仁慈的帝皇使者求饶,并且,是边吃边吐,边哭边嚎地去求饶。
阿竹则听着他们呕吐般的求饶,一屁股坐在他们崇敬的圣环殿上,打起了哈欠,摁压泛酸的眼眦,擦去两滴滚落的疲乏之泪,于星夜里高展双臂,笼身于月中,仰天大笑,嘲讽这些傻狗,骂他们活该当粪坑里的蛆。
是的,阿竹笃定自己的想法没有错,这种有胆的畜生,非得要狠狠作践,叫他们在茅坑好好反省。阿竹不信,在茅坑里吃上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在臭水沟吃一辈子后,这些棕皮还有种再犯贱。至于现在?吼吧,叫吧,越响越好,最好吼破天,叫这圣都、这世上的棕皮都听见,晓得伤害阿竹的朋友、不听班布先生的警告、冒犯帝皇使者的下场…就要比死更他妈的好玩。
笑完,阿竹的心平缓不少,便眺望圣都每处,去看给那嘶吼围绕的特罗伦人会是何种神态。可没多久便瞠目结舌,因为阿竹看远方的街上有熟人牵着手走在一起,下意识磕巴着叨念:
“葛阿姨?娜姐?他们在…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