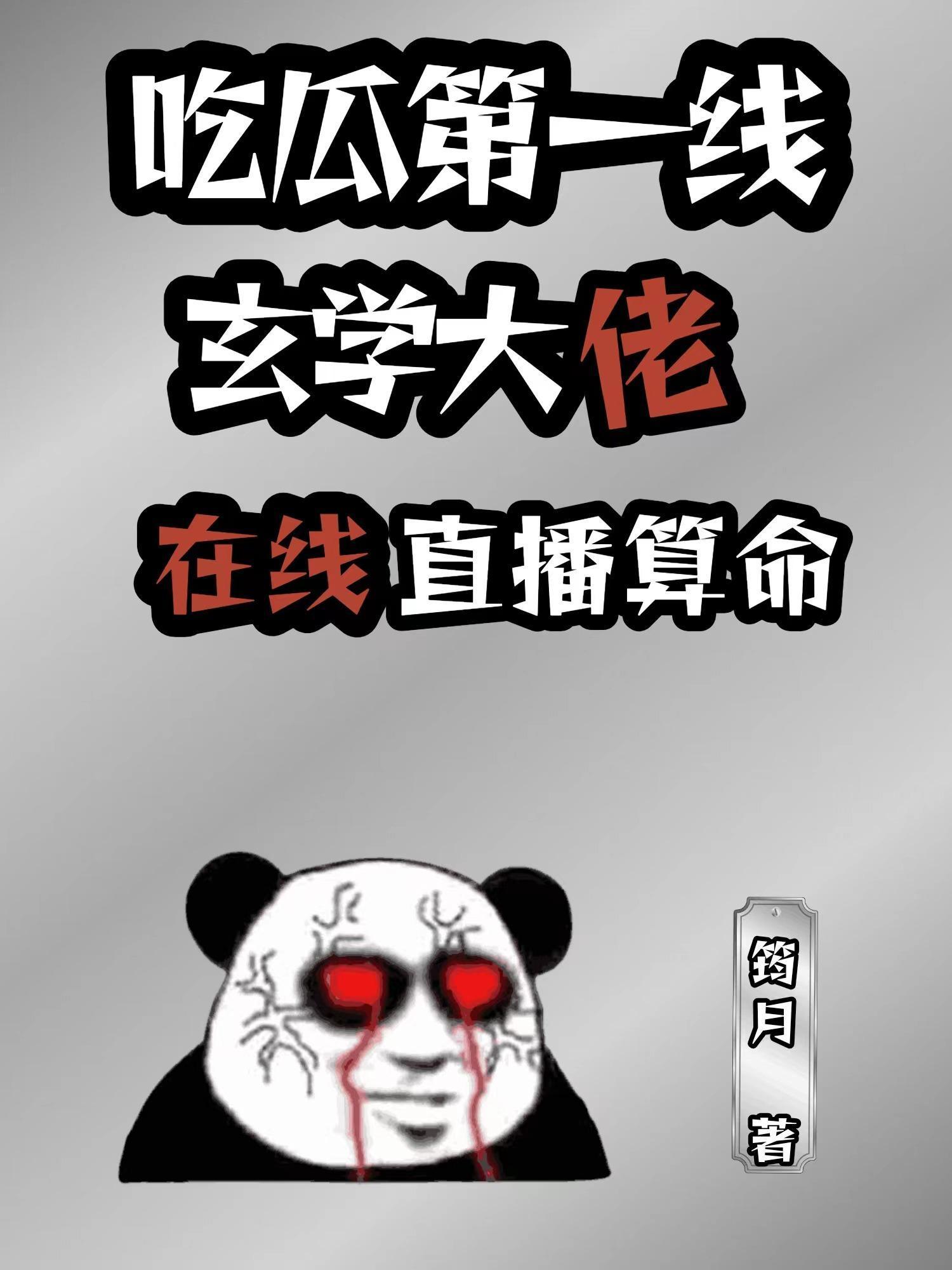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傍晚下雨潮水长的更急 > 第85章(第1页)
第85章(第1页)
我们是一体的。
她想装的不在意,靠近他那侧的耳廓出卖瞭她,微微的发红,好在室温不低,可以说是吃涮肉热的,也可以说是室内温度高所致,他没有问,她以为侥幸地躲瞭过去,并不知道在她侧著头故意不去看他时,他的视线已然捕捉到瞭。
也隻是暗香浮动月黄昏般,在眼底浅淡地染上一丝笑意。
也许是两人旁若无人的亲密还是让她有些稍稍的不适应,茉莉视线停留在牌面上,隻将头侧过去一点点,轻声问:“你看得出老太太什麽时候胡牌?”
模样像是考试作弊怕被抓到。
会这麽问,是因为茉莉之前听说过,有一类人在牌桌上精于算牌。她原先也是没想到的,听他说话的语气,突然这个念头冲瞭出来。
人的第六感往往是很奇怪的,就像此刻,他什麽也没说,她却好像有读心术一般,从他的眼神、语气、表情,从他散发在空气中的磁场,每一寸角落裡感受到、捕捉到。
而戴远知也仅仅隻是随意地说瞭一句:“看她拿牌就知道瞭。”
开局果然如他所说,老太太糊瞭牌,乐的眉开眼笑。倒不完全是牌桌上的几人让著,老太太在牌桌上的实力非同凡响,她是真爱打牌,年轻的时候创造过一个记录,一礼拜不睡觉光那打牌赚瞭一栋房子的收入。后来年纪大瞭,精力有限,可不敢那麽干瞭。洗牌的时候,宁储随口说起这件往事,还说戴远知在香港的时候但凡去老太太那儿就是打牌,切磋牌艺,刚开始还赢不瞭老太太,后面过瞭半年老太太的底牌都摸透瞭,就再没有输过。
戴远知笑道:“你怎麽比我还清楚?”
宁储道:“我每回来,老太太次次都会讲这事,都能背瞭。”
戴珍蓁仗著人多她二哥不敢拿她怎麽办,插话道:“我二哥最喜欢出风头,连老太太的钱都要赢。”
“这你就有所不知瞭,”
宁储替戴远知说话,“老太太对麻将是热爱,不喜欢搞那套让来让去的,你要是让她,她还不高兴。”
那刚刚他怎麽还说让老太太赢的话?茉莉在旁听著,心裡産生疑惑,怕是另有隐情,没好意思插话。
第二局赢的轻轻松松,期间,戴远知给她讲瞭讲基本的技巧,茉莉听得云裡雾裡,隻觉得像读书时候学数学,她最怕的就是这门学科,这轮结束成功把她听困瞭,于是她也不难为自己,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他,说要去卫生间。
一晚上她的帽子都戴在头上,没有摘下来过,也没人问起过她脸上的伤怎麽来的,连她自己都快忘记瞭。
茉莉也并不是真的想去卫生间,隻不过裡面温度太高,她半张脸一整晚都处在烧灼的状态,再不及时出来降降温,怕是要自燃起来瞭。
院子很大,有些年代的老房子,尤其夜逛,需要一些胆量和勇气。茉莉喜欢历史,连带著也热衷于古建筑,倒是并不十分害怕那些东西。这老宅院她来过几次,但都没有好好逛过,在夜晚和在白天氛围截然不同。
慢慢从前院逛到后院,又从后院到瞭前院,时间也不知过瞭多久,快到前厅的时候,依稀听到有人说话,打头是宁储的声音:“你在魏钧山的酒吧裡为红颜怒发冲冠,这事儿都传遍瞭,你是真的不怕?”
“怕什麽?”
语气听起来有一种凉薄的随意。
茉莉慢下瞭脚步,静然的夜晚,想不听到也很难。
“老太太这裡和我这裡,你带过来就带过来,都是无妨的,”
宁储担心道,“但是你再怎麽样也得忍忍啊,这个节骨眼裡搞瞭于少允,你是真不要命瞭,十年你都忍下来瞭,就为这麽一刻还忍不瞭瞭,远知,我以为你一向是最理智的。”
那头没响,接著是火柴划过的声音,戴远知点瞭一根烟。
宁储接著说:“不是说你现在不能对于少允动手,而是……茉莉,你要怎麽办,你别忘瞭,你隻是答应过你爷爷保护她,但没让你为瞭她这麽不计后果,就算你不为自己想,可为她想过?今儿酒吧一闹,你爸那裡,于傢那裡,谁还能容得下她?”
“要不还是把她送走吧。”
这一回他开口瞭:“送哪裡去?”
“送哪裡都行,越远越好,你可以赞助她读书,甚至她将来,一切的经济费用你都可以保障,但是你心裡要清楚,她在这裡,在你身边,没人能容得下她。不能让她成瞭你的软肋!”
“已经绑在瞭同一条船上,是不是软肋又有什麽关系,在我身边和送走,在哪裡都一样。”
他的声音很淡,很轻,缥缈的,还有一种让人难以抓住的消沉感,像是一阵风吹来就能飘走。
他好像自己也不确定最后会不会把她送走,没有定夺。
就像,客观事实并不能以任何人的意志所转移。
毋庸置疑,他是在意她的,也是喜欢她的,要不然怎麽可能这样举棋不定,舍不得又放不下,这样的黏黏糊糊。这不像戴远知的性格。
然而在茉莉看来,却也隻是到在意和喜欢的程度,仅此而已瞭。
茉莉站得腿脚发麻,瑟瑟的冷风灌进衣领口,直等到那边没有瞭声音,她才努力地抽回神来,面对现实。
这一刻,她仿佛才明白瞭金刚经的那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真正的含义。
茉莉并没有生他的气,隻是感叹命运这样的爱捉弄人,让她喜欢上瞭一个不可得的人。
她也曾想过,倘若他不是戴先生,隻是赤华,那麽兴许她努力一把还能够得上他。但是眼下、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