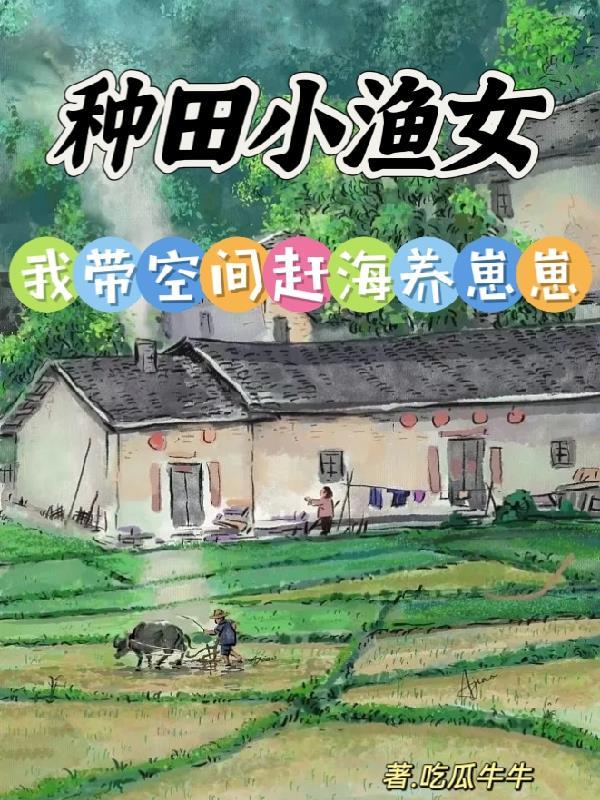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月明朝汐女主什么时候想起前世 > 第37节(第3页)
第37节(第3页)
细微的脚步声在耳边响起,荀玄微起身走开几步,颀长身形站在窗边,拨弄着昨日清晨阮朝汐新送来的冰花。是一朵栩栩如生的冰海棠。
“原来如此。你笃定一切都是假冒的,都是因为你阿娘对你说过的话,你全盘接受,深信不疑。”
他轻轻地笑了声,“但你有没有想过,你阿娘对你说的话,都是真的么?”
“为何不是真的?”
今日的屠苏酒确实喝过量了,阮朝汐感觉一阵阵地晕眩,和荀玄微的言语对峙令她极度不安,但她还是坚持说,
“那是我阿娘。她临终前还护着我,我陪她到最后一刻。阿娘为什么会对唯一的女儿说假话。”
荀玄微立在窗边,凝视着掌心逐渐融化的冰海棠,唤了她的大名。
“朝汐。以你的年纪来说,你过于聪慧洞察了。思虑得太多,洞察得太多,两边比对发现了破绽,便笃定是我这边不对。”
“但朝汐,你需知道,我对你绝无恶意。古人常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你如今尚年幼,倘若被你发现了你阿娘并不像你以为的、全心全意为儿女的慈母模样,你阿父也和你想象的完全不同,你阿娘对你说的话,十句里不见得有三句是真的……”
他把冰海棠放回窗外冰台上,关窗转过身来,“你会承受不住。”
阮朝汐混乱地站在原地。
阿娘和坞主,两边都是她深信赖的人,此刻却让她稚嫩的内心产生了剧烈拉扯。
直到白蝉带她出去,她一路始终保持着异常沉默。
————
阮大郎君在云间坞并没有停留多久。阮朝汐的猜测其实没有错,他确实是祭祀故人而来。
坞门高楼处,阮荻一身素衣,低头往下看。
白茫茫大地四野,缭缭青烟升起。凡人肉眼看不到的所在,或许有千百旷野鬼魂争抢殇食。
他突兀地问了一句,“他在云间坞停留了多久?”
荀玄微站在他身侧,缄默不答。
阮荻了悟,“你不能说?那我只问一句,他临终前可有留下什么遗愿?”
山风夹着飞雪吹过身侧,门楼旗帜猎猎作响,荀玄微依旧不发一言。
“这也不能说?”
阮荻苦涩地笑了笑,“罢了,我不再问了。今年祭祀事了,我明年再来。”
荀玄微领他走下门楼。
阮氏车队已经在坞门外等候。两人即将告别的前夕,荀玄微缓缓吐露一句,“他有遗愿嘱托我,我已应下他。你若信我,便不要问。”
阮荻一怔,眼角泛起泪花,郑重长揖到地。
即将登车返程前,他脚踩在车蹬处,回身又问,“十二娘之事劳烦你甚多。关于何时接她回阮氏壁——”
“昨日我与她商谈了。她谨慎畏生,这几个月在云间坞住得习惯了,便不愿轻易挪动。回阮氏壁之事,目前心有芥蒂,只怕还需多些时日准备。”
阮荻道,“人借住在你处,我是极放心的。十二娘年纪还小,缓几个月再回也无妨。若她准备好回阮氏壁,望你来信告知。”
荀玄微应下,又补充了句,“我即将离开豫州,入仕京城。以后的书信往来,只怕路上会多花费些时日。”
阮荻正踩着车蹬欲登车,惊得脚下一歪,差点从牛车上摔下。
“你你你欲入仕?!尊君那边如何说?你家二兄那边如何说?这偌大一个云间坞以后如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