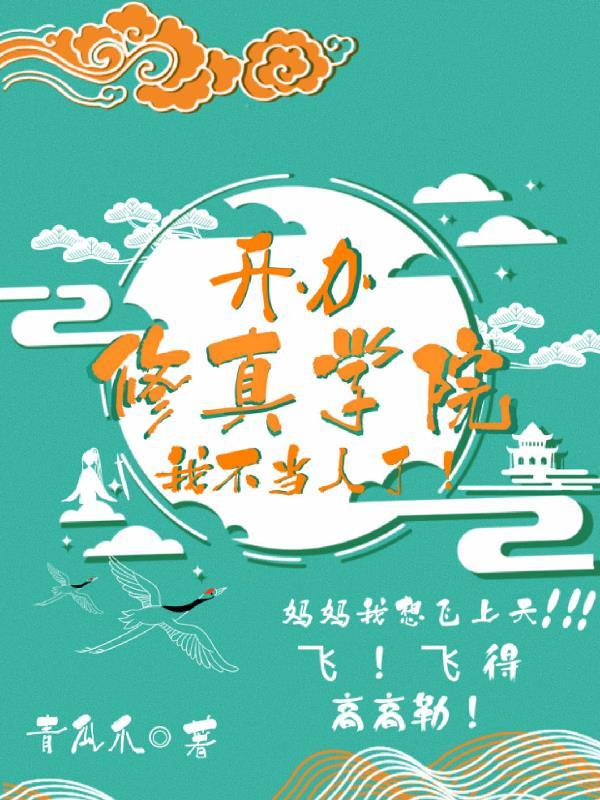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浮屠令gl笔趣阁 > 扶桑地(第2页)
扶桑地(第2页)
年少着恨道缘浅,而今但怨道缘深。
缘浅尚能凭修得,缘深进退不由人。*
不由人。进退牵掣左右难,从来都不由人。
*
一路从蓬莱回往浮屠,沿路夏花渐渐褪去,风沙肆虐,驱赶云层。
惟浮屠殿外那支兰花安在,白瓷的清纹蜷缩在叶脚,团成一片孤零零的影。
殿门大开。几日不见,殿内陈设已井井有条,宴如是坐在窗棂边,借了些许天光在擦长弓,眼见来人,她有些讶异地抬头:“尊……”
却是魔气侵袭,一只手抚上她双眼,恰遮住了全部光亮。游扶桑轻声道:“得罪。”
宴如是没有再问。魔气霸道,却也照顾了宴如是的状态,不会让她难受。
但仍有不解。
如今游扶桑与宴如是结成血契,理应神脉记忆都可互通。血契里,游扶桑为主,宴如是为客,那么游扶桑尽管锁着自己的神识,而可以探知宴如是的。
窥人记忆不是什么光彩手段,不过游扶桑入魔百年早忘了什么仁义道义,她只是太好奇方妙诚。
宴如是与方妙诚有仇,多次交锋,应当……
仅仅瞬息,游扶桑松开了手,她神色轻微地怔住,仿似探得了许多,又仿佛什么也没探明白。
宴如是的记忆与她从前所言相差无几。
许久未回宴门的母亲,再次出现时却背负了盗窃的罪名;青雾霭霭的宴门转瞬弥漫烽烟;逃亡路上风餐露宿,她捡起路边一只半碎的玉镯,茫然抬起眼,浮屠城的魔气在风沙里若隐若现。
正道的少主义无反顾扎进浮屠乌烟瘴气的城楼。
那么多灰头土脸的记忆,居然鲜少有方妙诚的身影。只偶尔几只信鸽,寄来一些血肉模糊的玩意儿,以示威胁。
游扶桑觉得怪异,总以为是哪里遗漏了信息……
但眼前宴如是与她干瞪着眼,显然在等一个解释。
她看着她,恍若又回到从前后山清雨落下,咫尺间一双清澈的眼。游扶桑倏尔有些心软,“抱歉。我借血契窥探了你的记忆。”
宴如是隐约一愣:“尊主可是怀疑我?怀疑我不忠不诚……”
她说话时脆弱地笑了下,语气还有些哽咽,眉眼低垂了,没有从前骄傲的样子。与魔修结成血契者最是心思不安,到处没有安全感,生怕被遗弃;莫名离别几日,再见时也只等到对方兴师问罪似的探查。
换谁都不好受。
游扶桑看着她,安抚的掌心终于还是落下了。
“没有的事情。我从未怀疑过宴师妹。”
*
游扶桑回浮屠,被关在书房里的庚盈如逢大赦。
“终于不用再抄那鸟书了!终于不用再抄那鸟书了!”
她欢天喜地重复了好几句,蹦蹦跳跳回到自己的小屋,春光满面,环视一周,细数自己的银针宝器,却惊觉比印象里少了些许。
她倏尔冷下脸色,抄起案边一只铃铛甩出房门,顿时听闻门外有人倏尔跪下的声音。
庚盈脾气不好喜怒无常是浮屠人的共识,哪人哪句让她听不开心,血溅三尺都是常事。曾有戏言:宁惹扶桑城主,也千万不要触这庚盈小鬼的逆鳞。
“是不是你?嗯?还是你?”
她一连着揪起好几个侍者衣领,一双眼睛里已经迸出恼火。
侍者跪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她们开始磕头:“给小的八百个胆子也不敢……”
岂料庚盈也不再追究了:“算了算了,算了!可能是我记错了。”
她摆摆手,松开人,显然是心情极好,“终于不用再抄书了,要去浮屠塔里大开杀戒啦!”
她那些毒针功效千奇百怪,无一例外伴随剧毒,稍不慎就是暴毙,旁人避之不及,庚盈也不觉得除开她还有谁能驾驭它们。也许是那几个魔修偷拿的吧……对着她的护法位置虎视眈眈,哼,趁她正被尊主罚着,来拿她的东西,找死!
庚盈在心里将那些人骂了百八十遍,盘算着等从浮屠塔里出来怎么报复人。
——自然不会怀疑到那位深居简出的宴少主头上。
同一时刻浮屠殿中,宴如是依偎在游扶桑怀前,佯作乖顺地道一声好。
暗处却眉头紧锁,乌黑的发里一枚短针寒如冷月。伴随着剧毒入体,无尽的疼痛如潮涨层层翻涌,然,功效却显著。
功效是……
隐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