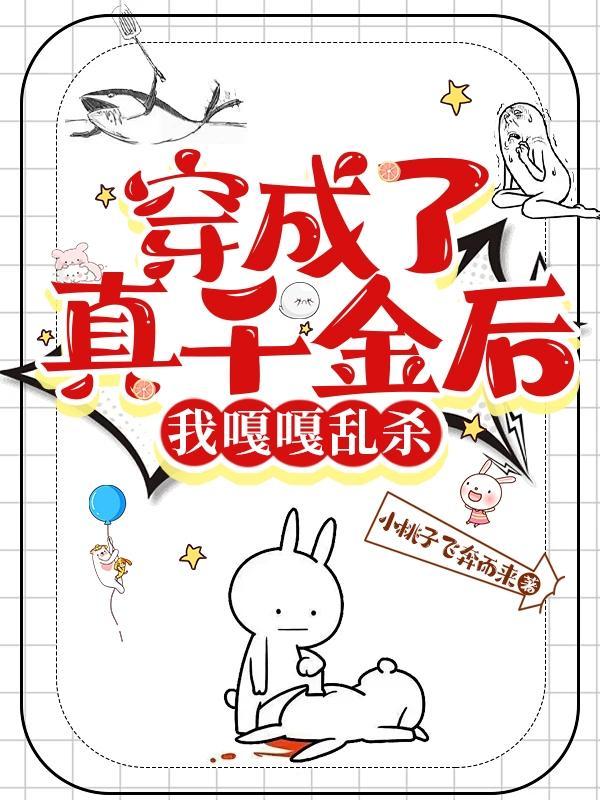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沾洲叹讲的什么内容 > 第37章(第2页)
第37章(第2页)
了一声,“就是想开。很想开。就好像……答应过什么人,要完成约定一样€€€€别往里了。”
贺兰破的指节停在他体内,听见这话便抬起脸,目光紧紧跟着祝神的眼睛:“约定?和谁?”
“没有谁。”
祝神屈了屈腿,“我不过打个比方。”
贺兰破抽出手,虎口掐住祝神腿根,拇指指腹正好按在他留下的一处吻痕上:“是不是他?”
“他?”
祝神皱眉,“谁?”
贺兰破指尖轻点,双唇抿紧又松开,视线在祝神脸上来回逡巡,仍不见祝神有一丝意会。这才定定开口:“那个戴帷帽的人。”
这话更把祝神说迷糊了:“什么帷帽?”
贺兰破见他依旧不肯承认,终于起身,绕出屏风,回到床边,自枕下摸出他一贯随身戴着的那枚铜钱,回到祝神身旁蹲下,搭着浴桶边沿,把铜钱递到祝神眼前。
“这我认得。”
祝神湿淋淋的手接过那枚铜钱,含笑道,“这是当年观音庙外,我给你祈福时扔进神龟池的铜钱。你几时偷跑去捡起来的?”
“这是他给你的。”
贺兰破观察祝神的神色,却见祝神在他说完这句话后愣了愣,接着脸上升起一股茫然。
想来是祝神也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对。
一是贺兰破不会骗他,二来,这铜钱并非普通铜钱,而是庙里专造来祭祀神龟的铜币,两文钱才能买来一枚,当年两个人有了上顿没下顿,有这两文钱祝神宁愿给贺兰破买个馒头,怎么会舍得投进池子。
贺兰破瞧他这样,眉间愈凝重:“你当真不记得了?”
祝神怔住。
十二年前的中秋,祝神突奇想,带着贺兰破去赶集,说是凑凑热闹。
那是在紧挨飞绝城的一处小镇,彼时贺兰家的长女贺兰明棋初得实权,一腔野心,年年带着贺兰军南征北战,不断扩张贺兰氏的版图。纵使整片洲土战火连天,只要在贺兰氏辖下的土地,百姓还能求得安稳的一隅。
小镇统共也就一条大街几支小巷,祝神牵着贺兰破笑呵呵四处晃悠,最后落脚观音庙前。
那庙是周边几处镇子最热闹的一处观音庙。传闻上一个百年的某个隆冬,一位贫寒书生进城赶考,路过这荒庙便进去休息。
入夜时他生起火,正借着火光看书,忽听门外有人喊他:“楚空遥?”
那书生闻声抬头,见门外站着个头顶玉箸,手提八角琉璃灯的小公子,生得俊眼修眉,看模样不过十七八岁。隆冬腊月里,也只穿一身单薄的青灰色衣裳。
他怕对方冷着,便赶紧往里让座,唤对方进来同他烤火。
小公子进来与他同坐,问他:“你要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