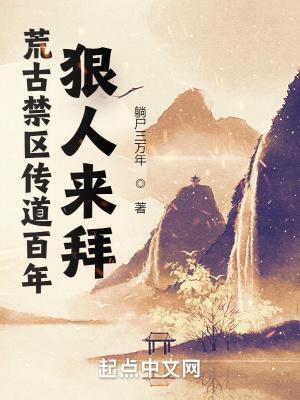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世子是个亲亲怪物 > 第51章(第2页)
第51章(第2页)
傅砚辞也跟着认真:“真的吗?”
“反正黎黎跟我说是这样子的,他们家乡那边有个说法,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是能知道外界生的事情的。”
“你现在打它,等出生后它会怨你的。”
傅砚辞夸张的惊呼一声:“豁,那看来这头崽子随它小爹。”
“什么?”
游青没反应过来。
傅砚辞瞥他的一眼,含笑道:“记仇啊!”
“疼!”
他捂着脑袋出一道惊呼。
游青收回拍他脑袋的手,美目含怒:“傅砚辞!”
游青提着他的耳朵质问道:“谁记仇了!?”
“我,我记仇!”
傅砚辞瞧着他神色终于活络了点,跟着他闹:“卿卿轻一点,等下为夫耳朵要被你摘下来了。到时候血淋淋的,多吓人啊。”
游青大慈悲,手上的力道松了松,抱着臂膀跨坐在榻上,忽的深深叹息一声,整张脸都埋在傅砚辞身上:“已经开始想你了怎么办。”
傅砚辞状似苦恼的思索着,指尖围着二人缠起来的丝打着转转,给了个馊主意:“要不我现在把身上穿着的里衣给你穿,这样你闻着我的味儿说不定就能睹物思人了!”
游青冷脸,毫不留情的拒绝:“我又不是变。态,才不会干这种事。”
“好吧……”
傅砚辞遗憾退场。
但到了次日,傅砚辞准备先行一步时,才觉昨日换下来的衣物不见了。起初他还以为是昨夜放外头被风刮走了,但到了早上帮游青掖被角时,在床榻里侧出现了一个衣角,他上去仔细瞧了瞧,看到了熟悉的纹路。
傅砚辞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没忍住在游青光滑的额头上落下一个轻吻。
游青在他走后缓缓睁开眼睛,睡到床榻外侧,又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七日后。
傅砚辞带着人正快马赶回军营,自从他从佃州先行后,许是因着佃州刺史的失踪给京城里的人带去了点消息,总时不时碰上规模或大或小的刺杀。
他忙着赶路,无瑕洗漱,浑身尘土,黑色外衣上更是沾满了鲜血。此时离军营还有三十里路程,但一行人均疲惫不已,身后更是还跟着一群狗皮膏药一般的黑衣死士。
拂袖回头看了一眼,低声骂道:“阴魂不散,都跟到这儿了。”
傅砚辞看了一眼身后的下属,深知再这样下去大家不被乱刀砍死也得虚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