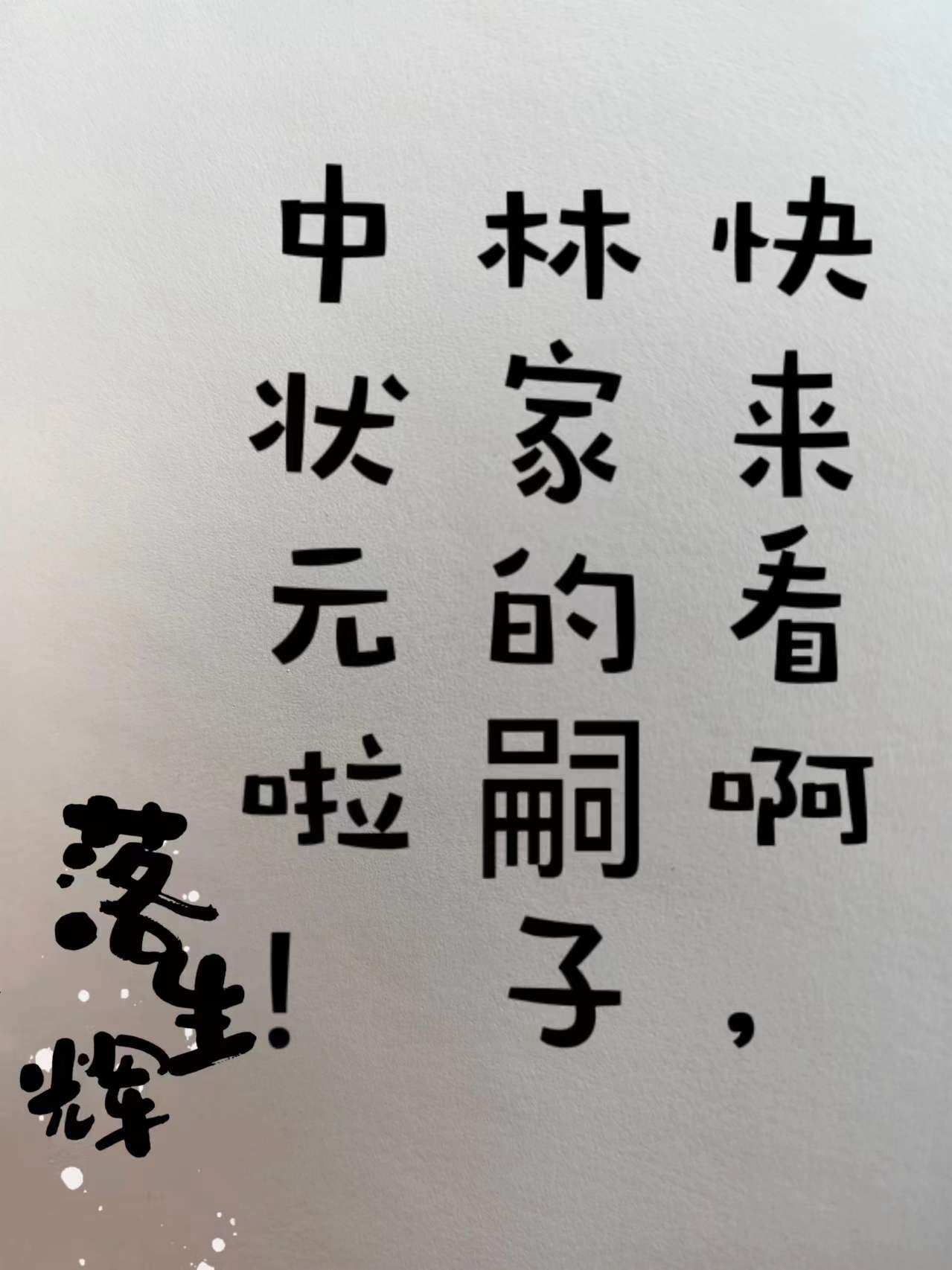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掌中雀by弃吴钩讲的什么 > 第46頁(第1页)
第46頁(第1页)
兩人無聲對峙了近三十秒,筆頭上的墨滴在雪白的宣紙上,砸出一團漆黑的絨花。
韓墨驍垂下眼,聽候發落。
第25章
梁今曦鋒利的眼神在他臉上遊走,像在選擇從哪裡下刀切進去。
許久後他突然笑了一下,讓步道:「寫一句。」
韓墨驍微微一愣,問:「寫什麼?」
「隨你,」梁今曦替他換了乾淨的紙,「剛說完不會再惹四爺生氣,馬上就犯錯,這可不好。」
韓墨驍接過筆,心裡弄不清這人到底是笑面虎還是冷麵佛。
剛才質問他還見了誰時,顯然是真的想殺人的;可他不肯接筆的那半分鐘裡,感覺自己被蛇信子舔了好幾輪,怎麼這墨一滴下,梁四爺的心情反倒又好起來了?
敢情那蟒蛇就愛舔人玩,其實是吃素的?
可是他確實不想再給人寫行書了,寫那副《將進酒》是迫不得已。
「想什麼?」梁四爺提醒道,「又要滴了,還想讓我伺候你筆墨?」
「哪兒敢。」韓墨驍想了想,下筆在紙上寫了三個字。
梁今曦
字體用的是小篆,不是他最拿手的,也算點畫單純、秀麗挺拔。
韓墨驍見梁四爺沒發話,自知這招偷梁換柱又惹了人家不高興,便裝模作樣地解釋:「四爺的名字用典雅端方的小篆寫最好看,只是我寫得不好。」
梁四爺拿過那張墨跡未乾的紙瞅了一眼。
這人的驕傲不容於世,如今倒還剩了一點,偷藏在心裡。
他將那張紙隨便丟在桌上,薄唇微動:「你在敷衍我。」
韓墨驍被當場拆穿,無處辯解,也不想悔改,低了頭道:「四爺罰我吧。」
梁今曦神情冷淡地看了他一會兒,上前把他攬進懷裡。
「韓墨驍。」
他總是帶點揶揄地喊「韓院長」,後來又仗著大他半輪,更是動不動就喊他「小韓院長」,這是第一次喊名字,聲音低沉舒緩,語氣冷淡,不帶絲毫感情,不過梁四爺的音□□人,自帶麻醉效果,聽著像情人情深意濃、耳鬢廝磨時喚的。
韓墨驍起先被他按著後腦勺將頭抵在胸前,聞言猛地睜大眼,心臟拳拳
跳動,耳邊空空作響。
「這幾個字怎麼寫好看?」梁今曦又問,胸腔隨著發聲輕微地顫動,還沒散盡的旖旎氣息將人緊緊籠住,給人一種溫柔的錯覺。
韓墨驍沒有抬頭,額頭抵著溫熱的身軀,覺得血液不斷地沖向胸口,擠壓得渾身發疼,幾乎無法呼吸。
他身上穿著梁今曦寬大的絲綢睡衣,上衣松垮垮地罩在身上,袖子是挽著的,褲子太長,踩了一截在腳下。
經由一天一夜的沾染,他的一切仿佛都被梁今曦侵占。
韓墨驍想起了那隻滾圓的「紅子」,想起那個精緻的鳥籠。籠子裡食住無憂,只需討好一個主人;籠子外面血雨腥風,卻有無邊蒼穹。
他抬手揪住梁今曦的衣擺,費力地吞咽了一下,說:「行草。」
說完這兩個字,他閉上了眼睛,又一次等候梁四爺的雷霆之怒。
然而梁四爺沒有如他所料,也沒要他當場寫出來,只是「嗯」了一聲,用力抱了他一下就把他推開,自己走了。
韓墨驍在書房站了好一會兒,覺得劫後餘生,又覺得腦子比身體還要疲憊。
被叫名字的時候,他幾乎要投降了。
又等了一會兒,韓墨驍的手腕快要被自己摳爛了,梁四爺還沒有回來,韓墨驍便走出房門,回到被拆得差不多的臥房。
他總是將脫下來的衣服也疊得整整齊齊,這次放在浴室的架子上,位置有些高,倖免於難,可以拿下來繼續穿。
收拾好自己,梁今曦還沒出現,韓墨驍按照來時的路往外走,路上遇到幾個傭人,倒也沒人攔住他問些什麼。
他和梁四爺在家廝混了一天一夜的事情,大抵已經上下皆知。
「四爺,韓院長像是要走了。」阿德站在梁公館深處的某間地下庫房門後,垂著頭恭敬地說。
庫房裡有好幾個到頂的博古架,上面擺著各種讓人眼花繚亂的收藏品和值錢玩意,一張歐式長沙發放在三個環形的博古架中間,對面是一面牆。
沙發背後的博古架另一邊,突兀地擺著一張醫療床,床邊還有幾個插著管子的儀器和一個看上去像鐵帽子的東西,一旁的小推車裡放滿了手術用的托盤和各類工具、器皿。
再旁邊是一個小的矮櫃,原本應該上了鎖,現在門開著,鎖還掛在門上,柜子里放滿了黑色的沒有標籤的藥瓶子。
梁四爺坐在沙發上看著對面那堵牆,等嘴裡的幾顆藥丸嚼碎吞了,苦味散去,拿過一旁點著的雪茄吸了一口。
「仔細送回去好好養著。」白色的煙霧裊裊向上,將他的臉隱沒了。
韓墨驍很快被阿德追上,二話沒說便乖乖上了車,只是身體太難受,拿了個柔軟的墊子墊在下面,但很快就歪倒在座位上睡著了。
吃下去的退燒藥或許早就開始生效,只是剛才太緊張、情緒起伏太大才抵抗住,如今終於泛濫了。
再醒的時候,逢春院早到了,阿德不在車裡,大概是等了他很久不見醒,自己下去透氣了。
睡了一覺沒有舒服一點,渾身反而更酸痛疲累,明天院裡的課大概率又得柳芽上了,韓墨驍慢慢撐著坐起來,發現身上搭了條毛毯,拿起來聞了一下,是梁四爺慣用的香水味,清冷又沉靜,像睡著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