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小说网>日月长明by > 第60章(第1页)
第60章(第1页)
阿癸拏仍旧看不惯这个可疑的中原人,觉得他不过是凭借花言巧语意图蒙蔽他们,所以态度依旧很恶劣,他粗声粗气地道:“你的两个同伴虽然吃了解药,但要好全还得休养几日,带上他们目标太大,不如让我的蛇儿吃了他们,省得碍手碍脚坏了事。”
老妪虽然没有附和,但从她神色来看,心里应当是同意阿癸拏的说法的。
明景宸道:“不用麻烦,你们找间牢房把人扔进去,每天给点吃喝别让他俩死了就成。”
他说得轻描淡写,浑然没把这两人的安危放在心上。
阿癸拏与老妪对视,心想这三人真的是一伙的?让两个中了毒的伙伴去蹲大牢,亏他想得出来。
没想到明景宸连应付狱卒的话术都替他俩想妥了,“你们只说这两个中原行商形迹可疑,未免他俩是镇北王的同党,坏了塔尔汉的大事,先把他俩收监,一来监视限制他们的言行,二来看是够真有人来营救他们好一网打尽立功。”
他说得滴水不漏,老妪看不出有何不妥,就对阿癸拏道:“你就按他的话去做,不得有误。好了,快点离开此地。”
说罢,她先领着明景宸出了神庙,往北行了半里路,在一处乱石阵后藏匿着一辆低调的马车。
两人上了车,车夫扬起马鞭呼呵着驱车离开了这一带朝月煌城的东南方向驶去。
也许是方才已经被面前的年轻人戳穿了自己的遭遇,也许是年纪大了,曾经心动过的男子早已作古,她数十年跌宕的人生又令她满含倾诉欲。老妪一改之前的讳莫如深,主动在路上将这些年生的事告诉给明景宸知道。
当年她第一眼看到宸王的时候就萌生了要与他离开的想法。不仅因为他这个人令她着迷,还为着他尊贵到能令野蛮的戎黎人以礼相待的身份地位。
那是她凄苦绝望的人生中能抓住的唯一浮木,能助她脱离苦海的神明。
宸王很心善,也很心软,他明知这个女奴远没有外表见到的那样天真烂漫,但还是愿意施以援手,花重金从商贾手上买下了她,并撕毁了她的卖身契还她自由。
还给她取了个好听的中原名字——素光。
素光知道一旦宸王离开戎黎,自己不仅守不住对方给的财物还会重新回到之前被视若牲畜的悲惨境地中,到那时再也不会有另一个宸王来搭救她。
所以她提出想随宸王去中原。
她有野心,有欲、望,她虽然喜欢宸王,但也想将他当作踏板得到地位名誉以及权势,她不要再做女奴,她要做人上人。
她想成为宸王的阏氏,虽然她不知道中原王爷的女人是否叫阏氏。
然而等她现宸王对她引以为傲的美貌视若无睹,三番四次并不接自己充满暗示的话茬后,她便果断放弃了去中原的决定,转投延谷诨的怀抱。
◇第93章天宝花开
太阳一点点升起,朝辉将马车内原本昏暗的光线慢慢点亮,老妪苍老的容颜彻底显露在明景宸眼前,依稀能从中窥探到几分当年明艳妩媚的少女风姿。
出于修养,明景宸并不多去看她的脸,只是心底突然想到了兕奴。
兕奴与素光差不多大,他如今又是何模样?
老妪也同时更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她愣怔了片刻,眼底有片刻的恍惚,接着后知后觉地将兜帽重新戴了起来,帽檐拉得低低的,将自己大半张脸遮挡住,然后接着诉说往事。
“宸王离开后没多久,老汗王死了,延谷诨顺利登位。起先我跟着他,不过是他众多女人中身份最低微的一个,甚至连宫廷都不能去,只被他偷偷摸摸地养在外头,用你们中原人的话来说就是外室。”
老妪说到这儿的时候故意停了一下,只用那双墨绿色的眼瞳注视着他,直到反复确认过在他脸上没有任何讥讽和贬低,才继续说道:“我时时战战兢兢,一边对延谷诨奉承讨好,一边还要防着其他女人的暗害,四年里我为他前后生了两子两女,如此才彻底稳住了在他心中的地位,他破格迎我进宫,封我为阏氏。”
“可他有很多阏氏,我没有母族,没有大臣支持,我只有我自己,我想要的得靠我亲手从别人手上抢回来。然而神明却并不让我如愿,眼看我的儿子就要被延谷诨封为王储,我所期盼的一切唾手可得的时候,我的丈夫、儿女全被塔尔汉杀了。他原本还要杀我,因我年轻时还有些姿色,便被他收了继婚。哦,收继婚你知道罢?哼,这种事在大漠各部族之中再常见不过,但你们中原向来自诩礼仪之邦,讲究礼义廉耻,这种腌臜事恐怕听都没听说过?”
老妪故意放肆地哈哈大笑,此时马车驶入喧闹的街市,两边叫卖声、牛羊嘶鸣声络绎不绝,笑声融入其中如同水滴沉入大海,了无踪迹。
明景宸不忍她这样笑,开口道:“你似乎比从前还要了解中原文化。”
直到这时老妪才露出得意的微笑,她不无骄傲地说:“我从中原来的行商手中买了很多书,还曾花重金聘人教我汉话,我虽说得不够好,但我认得你们汉人的很多字,比很多中原的贩夫走卒强多了。”
说着用汉话将左思的那《杂诗》从头至尾地吟诵了一遍,虽然口音很重,语调和句读多有些古怪,可比起从前大字不识的少女素光已令明景宸很是刮目相看了。
他由衷地赞道:“你学得很好。”
然而老妪下一刻又变了脸,问他:“你似乎对我很熟稔很了解,方才在神庙中我没多想,如今才觉出不对,看你年纪不过二十多岁,你出生时他都死了那么多年,你又从何得知这么多关于我的事,连我过去不懂中原文化都一清二楚?你们中原有托梦一说,该不会是他的鬼魂亲口和你说的罢。”
明景宸不欲在这个事上与她多说,便似是而非地敷衍道:“你可以这样以为,就当是他某夜入梦亲口告诉我的罢。”
老妪面色忽青忽白,一时难看至极。
过了会儿,她忽然嗤笑出声,有些反复无常的暴躁被她极力克制在眉宇间,等笑够了,她才道:“如果真如你说的那样他生前那般寄挂我,为何五十多年来从未入过我的梦,可想而知,你又在撒谎,你这个奸诈可恶的中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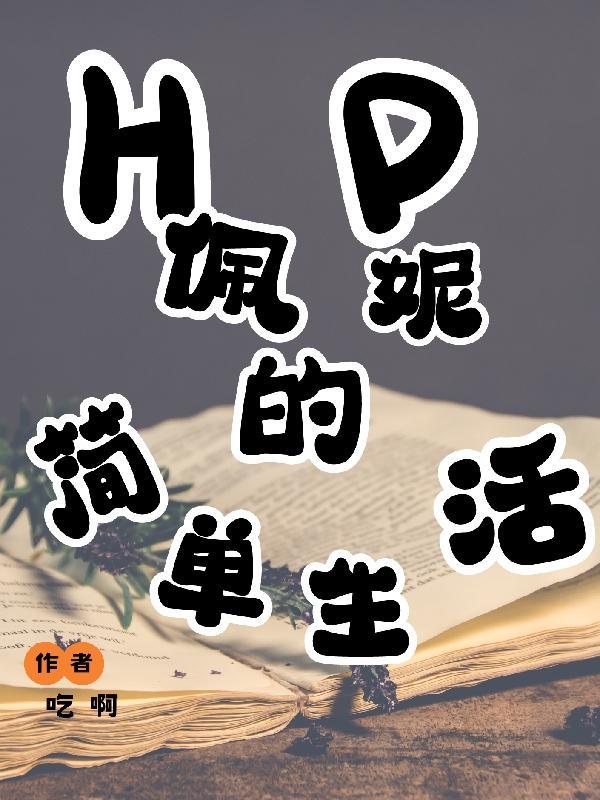

![[演艺圈]死灰不复燃](/img/2337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