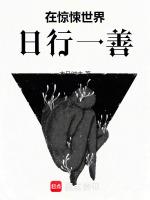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霍乱江湖by北南免费阅读 > 第 44 章(第2页)
第 44 章(第2页)
他无情拆穿道,“杜铮也这般伺候你我杀了他”
霍临风终于老实,拧一块布巾规矩伺候,不过抹香胰时又差点犯浑。洗罢,他用小毯将容落云一裹,返回卧房坐在床边抱着。
满室静,只那么两股呼吸。
容落云好奇地环顾,桃木桌,官窑的器物,蜀锦制的团枕撂在榻上。地毯花纹繁复,烛台鎏金泛光,这一屋子东西衬着将军身份。
再回想入府所见,一扇红漆门,两座石狮子,厅堂伴着六七偏殿。八九间小厢房,十来个小丫头,数不清的好物件儿细数完方觉千机堂的竹园有多寒酸。
出神想着,一股药味儿令他回神,霍临风打开了药瓶。他仰脸看对方,声儿不大地说“我杀死一头狼,夜里十几头来寻仇,都这么大”
钻出小毯比划,好似破壳而出的雏鸟。
又羞,赶紧拢拢遮住要害。“我用匕刺死几头,还一掌扣死一头,全杀光了。”
见霍临风没反应,再加一句,“狼嚎声都传到了瀚州”
霍临风破功“谦虚什么,都传到塞北了,惊了我爹的好梦。”
容落云拿挖苦当恭维,枕着人家的肩蹭一蹭,然后低头看腹部伤口。三四道伤痕,不知会否留疤,再瞄一眼胸膛,轻声絮叨“被揉红了。”
上药的手一顿,霍临风心猿意马“揉得你舒不舒服”
容落云赧然“不舒服。”
口中这般否定,心中却咂摸被揉搓的滋味儿,咂得自己生生软了筋骨。然后倚着人家,好诚实地改口“舒服。”
塞北人酷爱提问,霍临风又来“揉这个舒服,还是亲嘴舒服”
容落云小声答“都舒服。”
真臊得慌,撩起一角纱帐捂脸,声若蚊蝇地补充,“一边揉一边亲最舒服”
这他娘,霍临风低骂,莫非烫一下屁股把浪劲儿烫开了。
棉纱缠裹伤口,包扎完毕,他给容落云挑了身干净的寝衣。
容落云囫囵套上,宽宽大大的,袖子挽起几褶。躺好,月白丝被一蒙,只露一双犯困的眼睛,眨巴几下便轻轻合住。
睡得好快,犹如疯跑一天上炕就睡的孩童。
霍临风守在床边,待人睡熟才出了屋。“把脏衣裳敛走,再叫小厨备饭。”
他吩咐杜铮,“派人知会不凡宫一声,免得他们担心。主苑的下人不准进屋,你自己伺候。”
正说着,一名侍卫跑来“启禀将军,瀚州知府来访。”
前些日子邀对方一叙,没想到正赶在今天,霍临风即刻去迎。离开主苑,一路大步流星赶到头厅,进门便见沈舟端坐椅中。
他轻咳一声“沈大人久等。”
沈舟闻声抬眸,顿时一定“你是”
他笑答“我是霍临风,如假包换。”
朝暮楼踉跄一步,幸得对方相扶,沈舟忆起后大吃一惊。霍临风屏退下人,简明扼要地解释“当时在查江湖事,不方便透露身份,沈兄莫怪。”
沈舟逐渐回神,拱手行礼“将军言重。”
霍临风亲自斟茶“曾得沈太傅相助,得知沈兄迁任瀚州,便想见面一叙。”
沈舟愧不敢当“家父钦佩霍门忠良,将军不必感念。”
恰好他迁瀚州任官,也想与对方一见,因此收到书信前来拜访。
两人聊了许久,一武一文却十分投契,又仗着天高皇帝远而畅所欲言。许久,聊到瀚州闹灾一事,霍临风有的放矢地挑明些许。
“贾炎息竟是将军所捉”
沈舟惊道,“还有述罪状和账簿,帮了在下大忙。”
霍临风不欲抢功“我出点力而已,做主的另有其人。”
口中说着,面上情不自禁地含笑,“那人暂需休息,沈兄车马劳顿也需歇歇脚,明日咱们好好聊聊。”
沈舟闻言起身,他已命家仆在客栈等候,准备就此告辞。不留宿乃避嫌之举,霍临风明白,于是将人亲自送到门口。
晌午已至,霍临风顶着明晃晃的太阳折回主苑,小厅已布好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