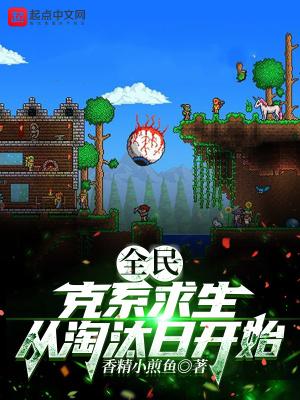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补天裂什么意思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这儿是阑珊,他的阑珊。
廊下是光洁而微凉的石的地面,安静地在面前伸延而去,廊外的藤蔓勃勃的生长,几朵细微不起眼的花在枝间叶底悄然地绽放——这毕竟是春天,无论如何的严寒之后都会来的春天,而花也就应了时,开也开不尽,在层峦叠翠间。
傍晚的阳光投来,透过枝叶的空隙,暧暧的抚着她的脸。眼前几枝新发的枝。叶间尚嫩嫩的带点黄,被光线斜斜的一照,直如了透明一般撩人可爱,在枝间还怯怯的打着几个蕾儿,柔软得几乎要随了她的呼吸轻轻地摇摆着,但始终在生长着,从不肯放弃。那将舞末舞的飘摇,引得几只虫蝶,流连不去。在廊下、柱边、花间、叶底。
她微笑了,嘴角微微地扬起,透出几分打从心底里的欢悦来。笑看着眼间的园子,枝叶扶摇的阑珊。园子出奇的安静,平和而淡静,一旁已看不到侍卫,只有阳光在穿过绿意的生长时,撒下簌簌的呤唱。虽是第一次来,却仿佛早就熟识了般,只感觉得到亲切,以及温暖。从心底缓缓地漫天卷地的浸透出来,暧过全身,再连带着给整个园子都染上些微的温暖,满心的温暖。
她在廊下安静地站着,带笑看着,看也看不够。直到天光缓缓地滤去。她才慢慢轻轻地移步,向着方才就被告之的方向走去。脚步轻轻地,怕惊扰了什么。然而他应该知道她来——
边走,边轻轻地数着,从这儿走到他的所在,一共有几步。有几个弯。其间有几根安静无声的玉柱。一共有几根藤萝已经长到了廊上来。而又有几根,要将她挽留下般,顽皮地抚过她的衣角——她精心地,盛装打扮了的衣角。以及在夜色中飞舞的几只小虫,太过于眷恋,忘了身处何时何地,忘了归去。一样样的数着,在心底里牢牢的记着。
时间尚早,然而前方已经亮起了光,幽幽的萤光,渐渐地代替了越来越淡得虚无地天光,凉凉地透出来,仿佛来接她似的,透着夜色中唯一的暧意。她微微地笑。他从来不用夜珠照明,也不用能将整个夜色照彻的幻术之类。只因为那样的光,也许终是冷的,死的。他宁可用那样淡淡的萤火,虽然淡,但是少冷一些,微暧一些。——很多他的事情,就如他对她一举一动了若指掌般的,她也知道。只是他不知道——她知道。
他就在前面,不远。她也不忙,慢慢地走,细细地数。待她走到那一点幽光之前,天光已静。一点幽光成了唯一的指引,就亮在眼前,心底,渐次地燃起一心的暧意。
她抱了琴,立在廊的尽头,再次地回头看了一眼,对着虚无一人的园子温柔的一笑。身后的夜色阑珊,掩在暗影里,却并不是沉沉的黑,那暗色竟还隐隐地带点暧,温柔地寂静着。原来,这就是他的阑珊,是这个样子的。
再不犹豫,甚至是带了点急迫的,轻轻推门走了进去。
门内幽光中,一眼看去,是一片淡淡的干净的白。纯洁的白,温柔的白,她最爱的白色,在幽光萤萤的房间里,到处绽放着,一簇簇地明亮着她的眼。让她在一时之间仿佛迷了眼,相看不厌。
白色是她最爱的,他却不大喜欢——这个,她也知道。
满屋是到处插着的,多到了几乎是遍地堆放着的纯白的夜芸花,随了她的到来,在她的眼间,一朵朵地渐次地开放,花气袭着她带入的清风,浓浓淡淡的袭人而来,香得醉心。一时间,满窒间都只是大朵大朵的白花,就在面前,纯色地绽放。
从没见过那么纯白,那么大,那么多,那么醉心的香的夜芸花,在同一时间,不顾一切地怒放着。让她的第一声不由自主的欢呼之后,第一反应便是要去将身后的门关得严严的,不让风吹进来。生怕这花儿被风一吹,便全如梦一般消散了。毕竟夜芸花是一生只开一次,一次只开一时的花。只为所爱的人,不顾一切地绽放一次的花,柔弱,却骄傲清丽。偏偏一不小心,便会被风吹雨打去。
慌忙之间,琴几乎要脱手滑下来,却又忙忙接住——这一掉下去,是要砸坏了花儿的。然而这一迟疑,便又连迈步也不敢了,就在脚下,也是怒放着的纯色的白花——
小心翼翼地掩了门,她却是如同少女般地微微仲怔着,就连面前榻上还有一人慵懒地依着,也几乎要视而不见。
“不要紧。”
那人却看得有趣,微微带笑开口。用了同样的时间魔法,才能够让这么多的花,同时的在她面前盛放。“今夜,它开在你面前,绝不会谢去。”
用着那样的魔法,耗着他本也时日无多的命,只为了这满眼的纯色大花能够开在她的心底。他所能够为她做的,欠了她的。
38
她这才一抬头,看到他半依半靠的歪在床榻之上,同样一袭淡淡的白,轻袍缓带。清得出了尘去。在淡淡的萤光之中,玉色一般地几乎要透明的人。
手支在床上,人却微微地仰起脸来看她,脸上神色淡淡的。疲惫慵懒而放松。微微地眯起眼来看她,深碧色的眼眸色泽更加深沉,隐隐地透出些黑玉般的润泽。淡淡的跟她说着话,神色也是极淡的,却是毫无掩饰的淡,平静而倦惫。把多年来从不曾在人前一露的倦意和萧瑟,全都毫不保留的展现在她的面前。只是虽然疲惫已极,然而终不肯绝望,不曾放弃过。
依然是展翅便能翱翔九天的白鸟,有着夺目的光彩,在纯白色的花朵之间也毫不逊色。美丽的骄傲着,疲倦的骄傲着。掩也掩不住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