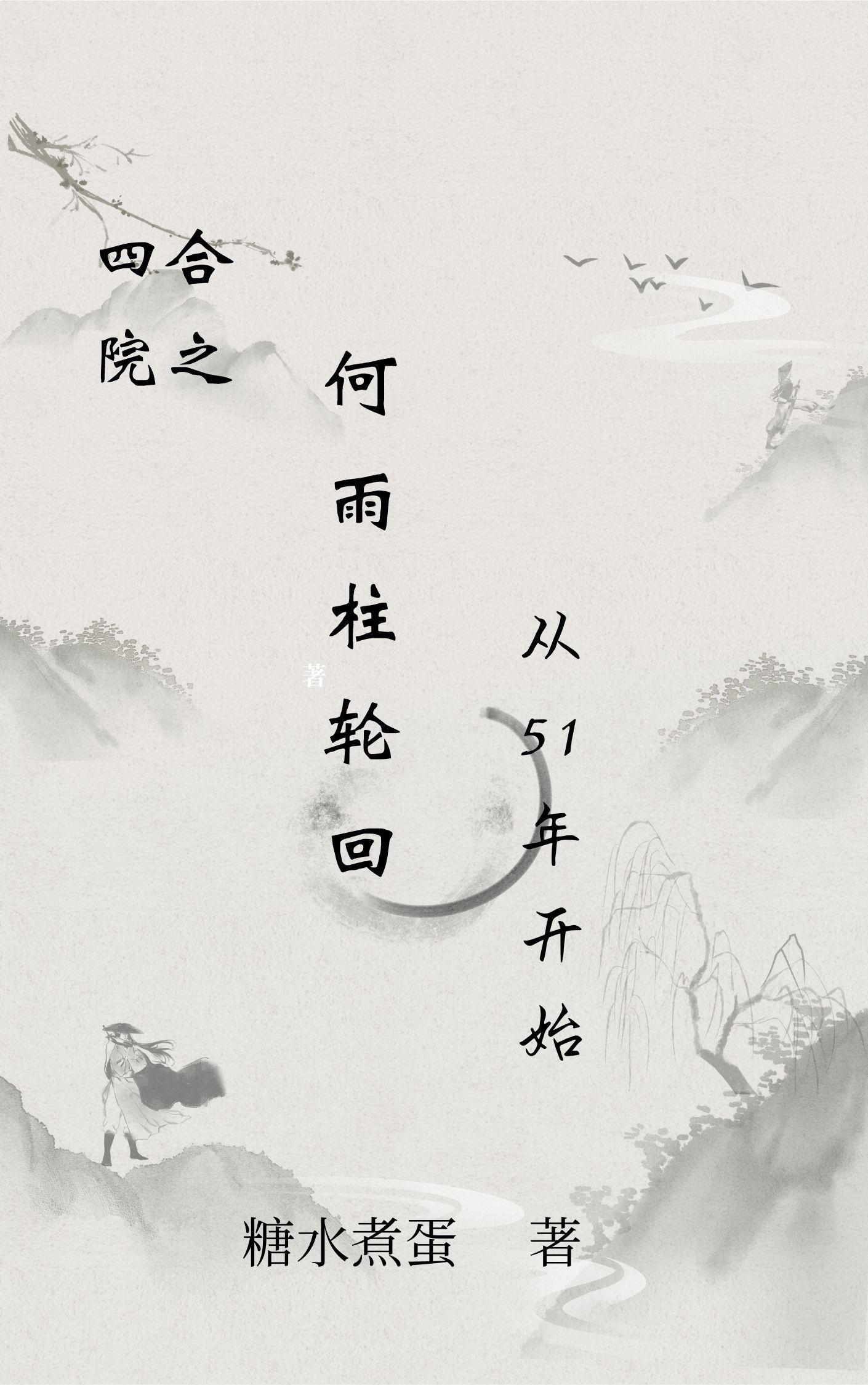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手足无错打一肖 > 第43章(第1页)
第43章(第1页)
静夜里,他听到隐隐的啜泣声,母亲的头贴在她背后,抚弄他身上的旧伤痕,静静地抽噎。
一个低低的声音喝斥:“你怎么来了?还不快回去?孩子大了,日后不要这么鼓弄他。”
秦溶心头一惊,不知秦老大如何来了他房里。
秦溶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却也听不到任何声响,也不知这老头子是走是留。许久,才觉得一只大手为他提上裤子掖好,再盖上被子,摸摸他额头轻声叹:“臭小子,这臭脾气,和爹一样倔。”
秦溶心里一阵酸意,但还是坚忍的咬牙坚定自己的决心。他不稀罕这里,更不在乎有什么家,有什么爹。
一个月来秦溶规矩地随了楚耀南出入蓝帮,在崇义堂上听差,一副归降的样子,反令秦老大松心不少。
只是他外出甚至去解手时身后都有“尾巴”
跟随,他知道秦老大并不十分放心他。
所幸有阿丹在,为他私下去跑青道堂通风报信,搞妥离开定江的船和从广州去香港的船票。
眼见日期将近,阿沛的伤也痊愈,家里风平浪静,那鬼也没有再出来过。
姨娘们都在窃窃议论,都说或是阿沛换了房间做噩梦,才恍惚中梦游摔下楼梯的。秦溶也渐渐相信,寻思着若秦沛肯安分惜福的住下去,秦府对他来说倒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
拂晓,晓星挂在天际时,府里下人都是鼾声如雷了。
秦溶推开窗,阿丹在楼下接应,他按照寻好的路径跃上树枝,翻过几棵树来到后花园,他不再走后门,而是跃身上了一段高墙,蹲在墙头再回首望秦府庭院重重,楼阁巍峨,心里一片落寞。心想,娘,别了,在这里当太太挺好,既是您喜欢,就暂且在这里,日后儿子混个名堂,就来接您离开。
秦溶走出几步,依依不舍地回头,仿佛对眼前一切无比留恋。步伐也变得沉重。
阿丹护了秦溶绕小道奔去江边码头。远远的汽笛声,卸货的挑夫号子声传来,时远时近。
不多时已经是天光大亮,码头上热闹非凡。
阿丹低声说:“溶哥去对面的茶楼等,吃些早点,我去安排妥了渡船就来接溶哥。”
阿丹离去,秦溶向茶楼去,忽然身后一声惊叫:“哎呀,这不是秦二少吗?”
秦溶慌得一个冷颤,回头看是方会长,是个买办,是青道堂的老主顾。如何见他就改称秦二爷,只得陪笑说:“方会长今日如何得暇来这里逛?”
“令尊秦老爷可身体康泰?”
方会长陪了笑脸,平日去青道堂运货时,这吝啬鬼都是大呼小叫疾颜令色的。
秦溶温煦地答:“秦会长尚好。多谢挂念。”
“代我问好,问好。”
方会长嘟念着。
秦溶敷衍他离去,心想那日才来洗三宴上看他笑话,见过秦老大,如今这么趋炎附势。又怕他嘴快惹来秦氏的人来追拿他,也不见阿丹回来,秦溶只得拉低帽檐直奔码头去。
嘀嘀嘀一阵喇叭狂啸,众人横七竖八乱跑如鼠蹿,笑闹声惊叫声传来:“左边,右边,快快,那边,歪了!哈哈哈哈哈……”
眼见一辆敞篷劳斯莱斯耀眼夺目地冲来,后面跟了一辆宾利和一辆敞篷老爷车。秦溶闪身避躲不及,一个白鹄亮翅跳去一边,那车嘎然停住。哎哟哟一阵惨叫,车上的男男女女惊得丢了魂儿。
“阿溶,怎么是你?你,你怎么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