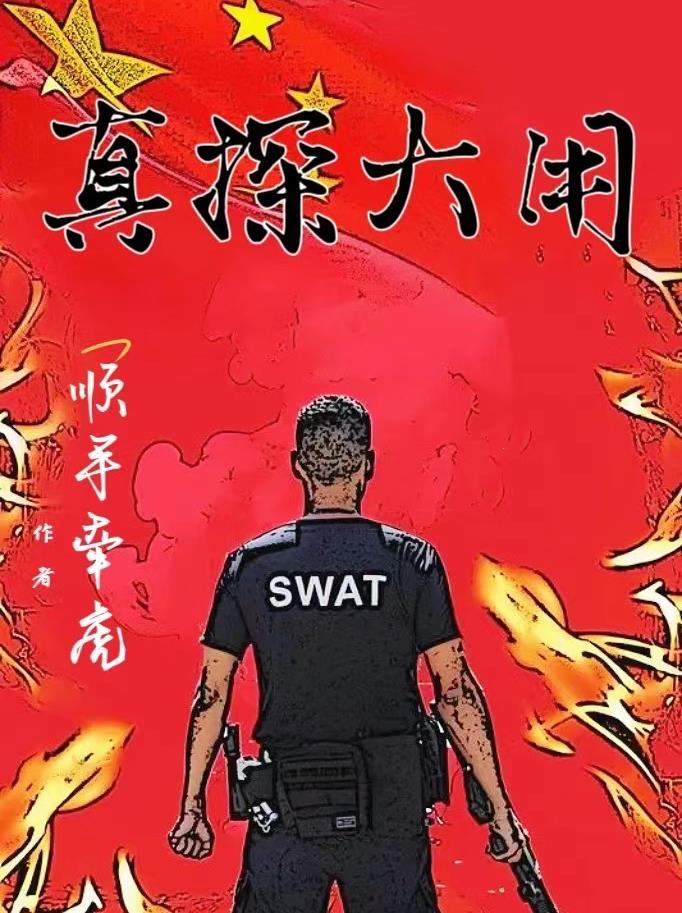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旷野的鸟讲的什么故事 > 第44章(第2页)
第44章(第2页)
当啷一声,有东西从谢濮手中掉落,然后咕噜噜滚到靳隼言床边,借着窗外微弱的光,靳隼言看清楚,那是一个酒瓶。
谢濮在喝酒。
一个说自己最讨厌酒的人,在喝酒?
靳隼言问:“你喝醉了?”
“我没有。”
谢濮反驳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眼花,靳隼言真的醒了,他匍匐着爬到床边,仰头看着靳隼言,“我没有喝醉。”
他想象过无数个靳隼言醒来的场景,愤怒地剧烈挣扎,或是怨恨地辱骂他,但都不像眼前这样,靳隼言如此平静,平静到让他不由自主感到恐慌,仿佛靳隼言早已识破了他的计划,看他就像看小丑。
“醉酒的人不会说自己喝醉。”
靳隼言手指碰到他的手臂,温度滚烫,“而且……你好像生病了。”
谢濮没有听清他的话,酒精让他的大脑一片混沌,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消减了他心中的恐惧,他终于敢直视靳隼言的双眼,打开灯,他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你先喝点水。”
谢濮的手在轻微地抖动,他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但靳隼言现了,胆小的兔子第一次做坏事,害怕是很正常的。
靳隼言注视他片刻,低头凑向水杯。
谢濮抬着水杯,喂靳隼言喝了半杯水,放下时,靳隼言的唇已经被润红。
谢濮垂在身侧的手指轻轻蜷缩,“你应该已经知道了,你现在被我绑架了。”
说得这么直白吗?靳隼言勾了下唇角,“所以呢?”
谢濮上前一步,膝盖碰到床,然后微微弯曲,他用两只手摁着靳隼言的肩膀,“所以你现在要听我的。”
高高在上的、对他冷漠的靳隼言现在就坐在他的床上,他可以对他做任何事,曾经靳隼言对他做的,他也能做。
比如亲吻,或是更加亲密的,能证明靳隼言真实存在,让他灵魂找到依靠的任何事。
锁链磕碰在床头,响声陡然变大,谢濮用力吻下去,嘴唇与靳隼言相撞,他感受不到疼痛,只觉得快意,酒精让他的思维变得迟钝,其余之外的所有感官都被放大,来自靳隼言的温度让他着迷,胸腔在悸动,温软的舌在交缠,他贪婪地攫取属于靳隼言的气息。
雨滴一下下拍打窗户,燥意加剧,靳隼言的手微微握紧,又松开,他听不到雨声了,耳畔只有谢濮的心跳,重得像是要砸穿他的耳膜,自己的身体在升温,他感觉到,神经在一点点融化,濒临失控的边缘,他掌心用力,扯着谢濮的丝将他拉开,吐息灼热,“你对我做了什么?”
谢濮并不回答,依旧抚摸他的脸颊和喉结,靳隼言的目光落到床头柜上的水杯,顿时明白了,“你给我下药?”
听到他的质问,谢濮慌乱地解释:“不会伤害身体,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
靳隼言眼尾猩红,胃部传来巨大的空虚感,眼前的谢濮成了唯一的食物,他忍着欲望,声音粗哑:“阿濮,我才现,你也挺疯的。”
是他小看谢濮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更何况谢濮本就不是真正的兔子。
“是你把我逼疯的。”
谢濮承认自己疯了,不然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看来你确实没醉。”
靳隼言的手指向上,触碰到他的脸颊,摸到泪水,是冰凉的湿润感,“你为什么在哭?”
连绑人和下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又为什么哭泣?
“对不起。”
谢濮哽咽着,他知道自己错得多么离谱,这件事如果被现,他不会有好下场,可他还是做了,“我只是太想要你了。”
他想要靳隼言,想得快要疯掉。
身体内的燥热在节节攀升,谢濮的眼泪成了最好的催化剂,靳隼言觉得有趣极了,想要看看这只兔子能疯到何种地步,他向后仰倒在柔软的被子上,轻声问:“阿濮,你想怎么要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