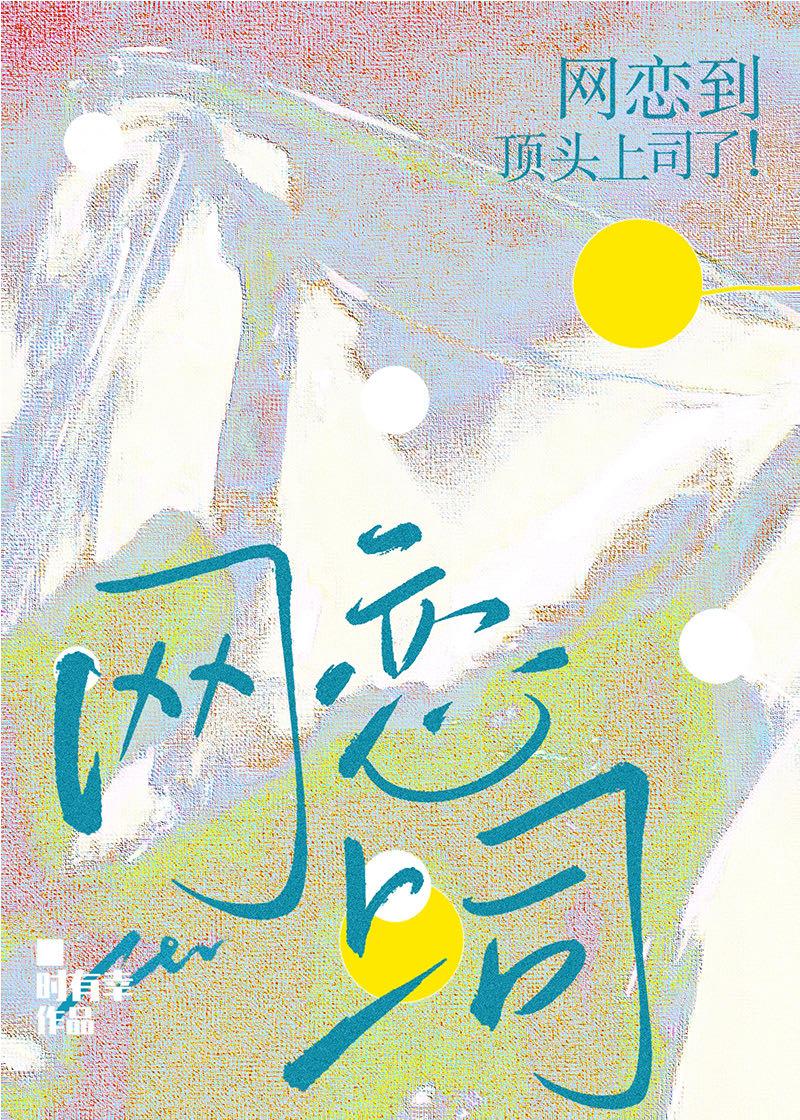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我家的田螺姑娘 > 第57章(第1页)
第57章(第1页)
这个老哥儿属实难缠,一张嘴叭叭个不停,嘴笨的刘柱子又怎么会是他对手,悻悻的带着刘柳走了。
赵显家的不死心在后面追着骂了几句,忽然想起来家来还有一个欠收拾的,连忙也不骂了,转身朝着家里走了。
大家一看人都走了,留在原地议论了一会也慢慢散了。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更何况村子里压根藏不住事,没消多久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村子,甚至其他村子也听到了风声。
小河村李家院子里。
李母正在院子里做衣裳,听到村里婶子说起来的时候,手下一错,险些将自己的手扎个血眼子。
李母不可置信的抬起头,直勾勾的看着李大婶,“你说的这是真的吗?刘柳真的做出这等事情?”
“我骗你干嘛。”
李大婶将手里的线放到嘴巴里抿了一下,把针穿到针眼儿里后说:“我有个侄女早些年嫁到了丰梨村,昨儿个她回来的时候说的,千真万确。
听说是当场被人家夫郎回来抓到的,两人光溜溜的睡在被窝里。
那家夫郎也是个厉害茬子,连衣服都没让穿,直接把人从床上揪下来,拖着就往村子里游示了一番。”
李大婶歇口气接着又道:“幸好你们给她送回去了,要不然在你们家里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这岂不是要羞死个人,老祖宗的脸都叫丢完了。”
李母听完叹口气,一脸复杂的看着院子里的某一处,脑海里全是刚刚李大婶的话,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自那天回到家里,刘柳整个人一点精气神都没有,眼神空洞洞的。
刘柱子一家人在村里都快直不起腰杆来了,走在路上都能听见别人都在后面指指点点。
饶是刘母也整日里唉声叹气的,嘴里不住说着:“造孽啊造孽,我怎么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检点的女儿啊!这刘家的脸都让她给丢尽了。”
刘柱子媳妇听后心里充满鄙夷,却也没在说什么。
但没过多久,村里就有人传出风声来,说那刘柳又要嫁人了,嫁的夫家还是对面落霞村。
“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真如大家所言,以后终归有个依靠,她离开了这里,别人说什么她也听不到了。”
“好什么好呀!”
溪哥儿放下怀里的狗崽,嘟着嘴不赞同的说道。
宴清霜这才想起溪哥儿也是落霞村里嫁过来的人,刘柳要嫁的夫家恐怕他也认识,于是急忙问道:
“到底怎么了?难不成那人是有什么问题吗?”
溪哥儿摇着头叹息一声,也忍不住悲悯起刘柳来。
“那家人在我们村上可是出了名的蛇鼠一窝,婆婆不慈,老公公也没个正形。”
“家里孩子多妯娌也多,大多都是不好相与的人。一大家子也没分家,整日里为着个鸡蛋都能吵起来。”
“而且刘柳要嫁的还是那家的三儿子,那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整日里不是喝酒就是打人,他前面几个夫郎和媳妇都是被他打跑的。这刘柳要是嫁过去,估计也是捱打的份。”
拾掇
唉!以后的事谁也不知道,可这日子总归是过出来的。
天还未亮,刘家院子里微弱的火光燃起,刘柱子夫妻以及刘父三人将刘柳送到村口。
刘父将一个装有衣物的小包袱挂到女儿手臂上,眼里湿润,他刘大是个没本事的,帮不了女儿什么,只盼她以后能苦尽甘来,好好在夫家过日子。
刘柳神情麻木,手臂上的包袱虚虚挂在手腕上,天还黑着,她眼神呆滞的看着前面的泥泞小路恍若没有尽头,心里无端生起一股怨恨。
一家人就这么等在村口,等到小路那边终于骂骂咧咧的来了几个人,将刘柳接走了。
村里的事无论好的坏的都时有发生,今天是刘柳,明天就是谁家里的一颗鸡蛋。
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成为村里人的新谈资,刘柳这事也会随着她的离去慢慢淡掉,偶尔想起来,或许也会在谁家的饭桌上说上那么一嘴,但总归不如现在这么剧烈。
“相公,桶里面不是还有几条小鱼吗?你把它们处理一下我待会给炸了。”
上次的大鱼一拿回来就被吃了,还剩下一些小鱼养着,顾庭风听到夫郎唤他,忙放下手里的柴火把鱼提到院子里宰杀。
这些鱼大约都只有三指宽,去掉内脏和鱼鳞就没剩多少肉了,不过胜在量多,顾庭风清理出来一大碗,拿到灶房去给夫郎炸。
宴清霜见鱼处理好了,往里面撒上一点盐,放上几片姜蒜和紫苏腌一会去腥。
趁这功夫,又拿了个大碗准备捞些酸菜,上次他和溪哥儿摘得水芹被他做成了酸菜,现在已经可以吃了,捞出来用清水洗一下切段,和个蘸水直接吃就行。
腌好的鱼因着太小,没有直接炸,而是放进面糊糊里滚了一圈,等鱼全身包裹上面液才下锅炸,炸到两面酥脆焦黄再夹出来。
顾庭风闻着味进来了,“好香啊!”
宴清霜用手捻起一条小鱼凑到他嘴边,“尝尝,小心刺。”
虽然刺都被炸酥脆了,但是这种小河鱼刺还是很多。
“好吃,很香,还很脆,”
宴清霜看他哈着气嚼着小鱼,轻笑一声,轻轻推了他一把,“马上就开饭了,快去洗手。”
顾庭风看了一下自己刚刚劈过柴火的手,笑着转身洗手去了。
两人吃完饭就下地干活去了。田地里的庄稼都长得很好,再过些时日就能有新鲜果蔬吃了。
顾庭风和夫郎花了几天时间给它们都追了肥,除了草仔细打理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