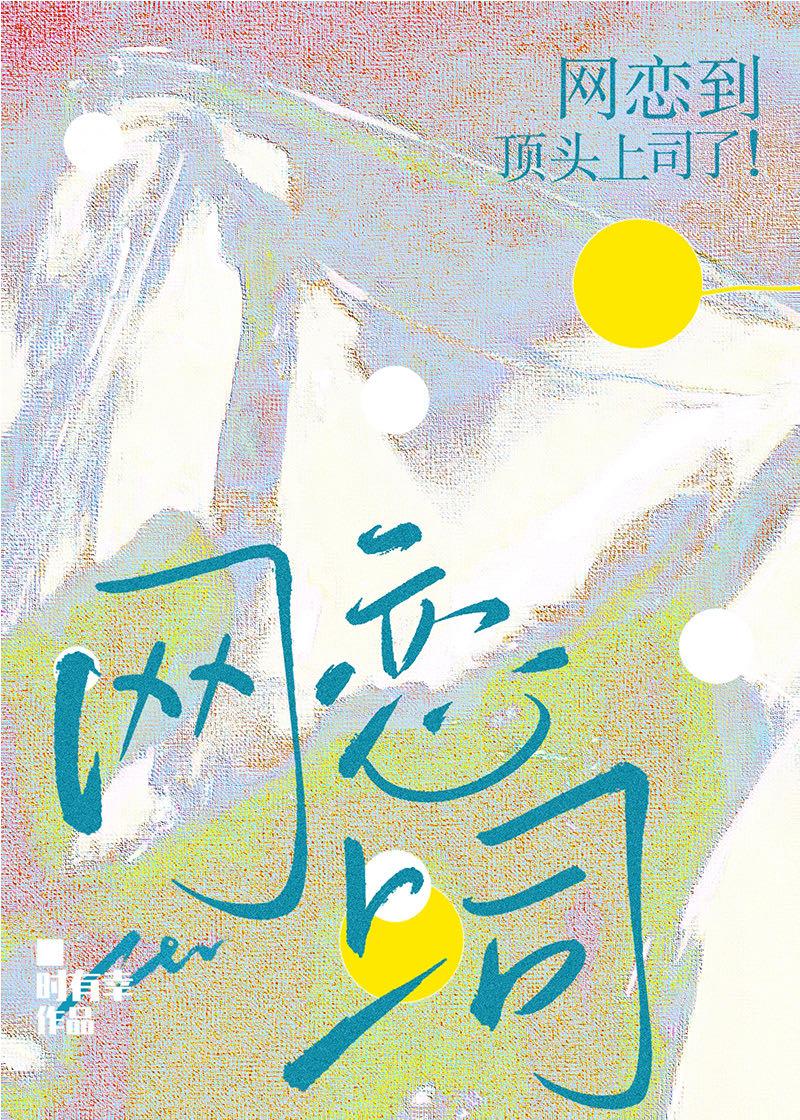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我在星际卖烧烤免费阅读 > 第52章(第1页)
第52章(第1页)
“喏,周旭你瞧,那就是那个捡破烂的。”
“看吧,我就说他每天都要来这儿捡瓶子!”
“哈哈哈哈哈怪不得,班上总是有股臭味,原来是他身上的啊!”
纪乔怔怔地站在原地,任由他们簇拥着中间的少年对自己指指点点。
那些声音越来越肆意,他的脸颊逐渐烧得通红,抬起手臂闻了闻。
蓝白色的校服很整洁,是清新朴素的肥皂味,一点也不臭。
这样的嘲笑时常发生,纪乔知道他们故意取笑,也知道最中间的少年据说家里条件不错,反正都是自己得罪不起的人。
他再不高兴,也只是抿着嘴,把头埋得低低的,拎着蛇皮袋从他们身边快速走开。
纪乔天真地以为,那不过是放学时的小插曲,然而他真正的恶梦很快到来。
之后再去学校,他的作业莫名其妙被撕得稀烂出现在垃圾桶里,水杯时不时地出现粉笔灰,去食堂打饭时也会突兀地被人狠撞一下。
全班的人好像团结在一起,把他排除在外,让他像只无措茫然的幽灵在教室里徘徊。
为什么呀?
我有做错什么吗?
纪乔很难过,他想不通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这么糟,又很快收拾心情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忍一忍就过去了。
第二个月交班费时,班长突然说收齐的班费不见了,所有人的视线齐齐投向刚走进教室的纪乔。
“还用问吗?肯定是纪乔!”
“全班就他最穷,连班上的水瓶子都要捡……”
“翻他书包吧,塞那么多东西,怕不是还藏了别的!”
周遭的气氛隐隐有些不对,纪乔不知所措地退到墙角摆手,摇头嗫喏着:“我没拿……真的不是我啊……”
可惜他的声音在众人的讨伐声中如此渺小微末,书包也好,书桌抽屉也好,像是被抄家似的全被翻了一遍,就连他自己也被几个男生嘻嘻哈哈地压在墙壁搜身。
最后除了几张皱皱巴巴的零钱,什么都没有找到,纪乔甩开按住自己的人,红着眼朝他们怒吼:“滚开!都说了不是我!”
所有人哄笑一团,周旭只是懒懒地说了声:“哎呀,好像误会了,纪乔你别介意啊,就当是玩笑好了。”
他们一群人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般,又呼啦啦走开,纪乔低着头,仅存的那点自尊和满地破烂不堪的书本卷子般印满污黑的脚印。
冰冷的手指贴着裤缝微微蜷缩,大滴大滴的眼泪珠子砸在纸页发出嗒嗒声。纪乔偏头擦干眼泪,蹲下身慢慢收拾一地狼藉。
等到放学时候,周旭在回家的路上被人套了蛇皮袋狠狠地打了黑棍,他气急败坏地扯开脏臭的口袋,却没瞧见半个人影。
之后的事就一发不可收拾,谁撕纪乔卷子,纪乔就撕回去,锁厕所也好,走路被撞也好,别人怎么施加在他身上的,纪乔全都加倍返还。
次数一多,许多人都对他身上那股不管不顾的狠劲生出些许畏惧,只有周旭像是找到了一个新鲜持久的玩具,带着人将他压在地上打得爬不起来,纪乔越是反抗,那些拳头巴掌就落得越起劲。
他问周旭为什么是自己,周旭眼睛亮闪闪地说——
你看起来比较好玩啊!
每天晚上,纪乔缩在被窝里发出呜咽的低音,他也期望过有人能救救自己,像是动画片里闪闪发光的英雄从天而降,可惜从来没有人回应过他。
难熬的高中生活就像塑料膜覆盖在脸上,裹得他密不透风喘不过气,像具行尸走肉般想着过一天算一天。
无数次反抗后,周旭对他的兴趣不减反增,带人将他堵在巷子打算施暴时被居民楼的老人发现,打了报警电话。
所有罪责都被推到了纪乔头上,没有人付出任何代价,反而是他被学校退学,像是垃圾般被扫地出门。
奶奶知道了原委,没有怪他,搂着他泪光闪烁:“是奶奶没有用,都不知道我的乔乔受了那么多苦……那么多伤…他们怎么、他们下得去手!”
“没事。”
纪乔窝在奶奶温暖的怀里蹭了蹭,扬起脸笑道,“奶奶给我煮个鸡蛋,我吃了鸡蛋就不疼。”
那年夏天,学校缩短了假期,许多准高三生哀声载道去补课,纪乔没再找学校,不是他不想上,而是奶奶病倒了。
医院人多混乱,他自己也没进过几次医院,背着水壶和旧挎包,像只无头苍蝇般攥着挂号单乱跑。
他怕奶奶跟不上,让她去座椅上等自己,老人家得了癌,手术和化疗方案听着纪乔头晕脑胀,医生也看得出他不过是个半大小子没什么能力,只能问道:“你家大人呢?”
纪乔说:“没了,我就是大人。”
手术还要大笔钱,医生先给他开了药,他刚坐下屁股又得挪起来,好不容易跑了几层楼拿完药,护士小姐又告诉他暂时没有多余的床位。
纪乔说走廊也行,回头去找奶奶,结果当他回到休息区时又没看见奶奶的身影。
他疲惫地叹了口气,无力感顿时席卷全身,可又来不及崩溃,找护士和医院的保安帮忙,总算在一楼大厅找到了慌张无措的奶奶。
“你跑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跑!”
纪乔红着脸,泪水奔涌而出,“不是让你在那儿等我吗!”
奶奶也哭了,拉着他像个犯错的小孩般道歉。
她说乔乔我的病好贵,咱们不治病了行不行,钱要攒着,攒着给你上大学呀。
“不上了!我不读书了!”
纪乔痛哭着伏在她身上近乎哀求地哽咽,“不上大学我也能赚钱,我能赚好多好多的钱,求你、求你再陪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