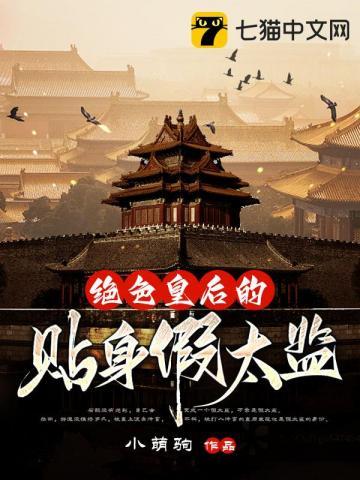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和恶魔做交易没好下场 > 第34頁(第1页)
第34頁(第1页)
「那你可要努力了。」惡魔滿不在乎的擺擺手,把她放在床上。
……
「我不喜歡戰爭。」忘了是哪一天了,在他位於阿爾卑斯山間的別墅上,一個難得閒暇的午後,他們站在露台邊上,瑞貝卡說。
「沒人喜歡戰爭。」ado1f說,他正逗弄著他剛送給她的兩隻德國牧羊犬,「但我需要轉嫁社會矛盾和國內矛盾,人民現在過上了好日子不是嗎?」
「除了猶太人?」
「除了猶太人。」他笑起來,深深地看著她,不無驕傲的開口,「是歷史選擇了我,是德國人民選擇了我。」
「然而這依舊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你對猶太人做的,將來一定是會被後人批判的。」瑞貝卡撐著頭,食指在空中點了點,抱起腳邊的小狗崽親了一下。
「我知道,但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假如我贏了,過個幾十年我做的錯事就會被時間抹去,那時我為德國人做的將是不亞於俾斯麥和腓特烈的,親愛的約翰娜,別高估群眾的記性。」他俯視著貝希特斯加登,「假如我輸了,假如我輸了…我不能輸。」
「你會贏嗎?」瑞貝卡忍不住笑了,「老實講,我只喜歡你前幾年幹的事,然而德國現在就像一列高行駛的火車,裹挾著民族主義,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畸形發展了十幾年,它註定要駛向戰爭,死亡和毀滅,誰也無法讓他停下,勝利與生存緊緊綁在一起……」*
「民族與民族之間從來不是零和博弈。」瑞貝卡最後說,「你不能在自己這一輩子就把幾百年的事做成。」
「假如我贏了,就一定可以。」他堅定而決絕的說。
當1945年,ado1fhit1er於地堡自殺前,他從幾十年來關於國家、民族和戰爭的大夢中突然清醒過來,不幸的是他輸在了最後一步,幸運的是他輸在了最後一步。
他回憶起那個下著雪的閒暇午後,想起小約翰娜常年因抑鬱而顯得蒼白病弱的面孔,對密施下達了最後一個命令。
「把我葬在柏林大教堂。」
--------------------
*來自歷史調研室
第18章約翰·施密特
=============================
——感情很顯然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之間,而且常常是在我們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突然發現的。(米蘭·昆德拉)
七歲的約翰·施密特與他的妹妹相依為命,貧窮與飢餓兩個一戰遺留下來的陰影終日盤桓在這個德國的小村莊裡,當母親在生妹妹而難產去世時,他就像個局外人一樣,靜靜的看到他的父親號啕大哭,隨後他又看著自己剛剛被剪下臍帶的妹妹,她滿身鮮血,孤零零的躺在那也大哭著,接生婆為她洗去皮膚上的胎脂和鮮血,露出了她本來的面貌。
「醜死了。」小施密特看著她皺巴巴的小臉想,但他沒有說出來。
當他反應過來的父親試圖淹死她時,施密特猶豫了好一會到底救不救她,那個男人瘋狂的愛著他的妻子,連他的兒女都視作阻礙。
……然後他們被送到了孤兒院裡
面對修女的詢問,他忽的想起當他第一次被母親領著進入教堂,慈眉善目的神父送給他一本拉丁文寫的聖經,他不信教,但還是不情不願的道了謝,翻開後就連看也沒看的隨手指著上面的一個詞問,「這是什麼?」
神父無奈的笑了,「瑞貝卡。」
施密特紅了臉。
「她的中間名叫瑞貝卡。」他告訴修女,無傷大雅的撒了個小謊,「我母親臨死前訂好的。」
……
施密特有那麼些個時候很想掐死她,但從瑞貝卡平安長到十幾歲來看,很顯然他都沒有下手。
他第一次想要掐死她時他們剛被送進孤兒院,當他的手一點點在嬰兒那軟綿綿的小脖子上收緊時,小瑞貝卡笑了,朝他吐了個泡泡。
「……」
當小瑞貝卡七歲時,施密特就帶著她從孤兒院跑了,她是個累贅,毫無疑問的,未來的美貌在這時就已經可以窺見幾分,孤兒院的嬤嬤和孩子就沒有不喜歡她的,一個美麗的小廢物對他確實是個大麻煩。
「要不哥哥把我丟下吧。」瑞貝卡弱弱的開口,哭唧唧的說,「我拖你的後腿了。」
「知道還那麼多話。」施密特認命的把她背起來,掂了掂,覺得還能接受,看著她發紅的眼睛,「我不會把你丟下的。」
——他永遠也不會告訴她那天他差點真的就照做了的。
「我們去哪?」瑞貝卡打了個哈欠,心中一點也不認為離開孤兒院是個好選擇。
施密特沒有回答,於是瑞貝卡又摟緊了他的脖子,安穩的睡了過去。
在與貧窮、暴力和不讓人省心的施密特度過八年以後,她的哥哥終於安定下來,望著自己顯然已經長成朵嬌花一樣的半大的妹妹,終於踏踏實實的找了份旅店跑堂的工作,雖然日子還是很貧苦,雖然他們兩個人還得擠在一張床上,但好歹他們終於能有個能正常睡覺的地方而不是擠在地板上了。
這份工作給了施密特一個極大的機會,阿蒙·戈特很賞識這個年輕人,他從他冰冷的藍眼睛裡看出勃勃的野心與暴戾來,於是機會就這樣戲劇性的來了。
這個年輕人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狠勁,在阿蒙的有意栽培和自身的努力下,他很快就成為了他的心腹,在這個過程中,他和瑞貝卡住上了小但乾淨的房子,她把那裡打理的井井有條,讓施密特恨不得天天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