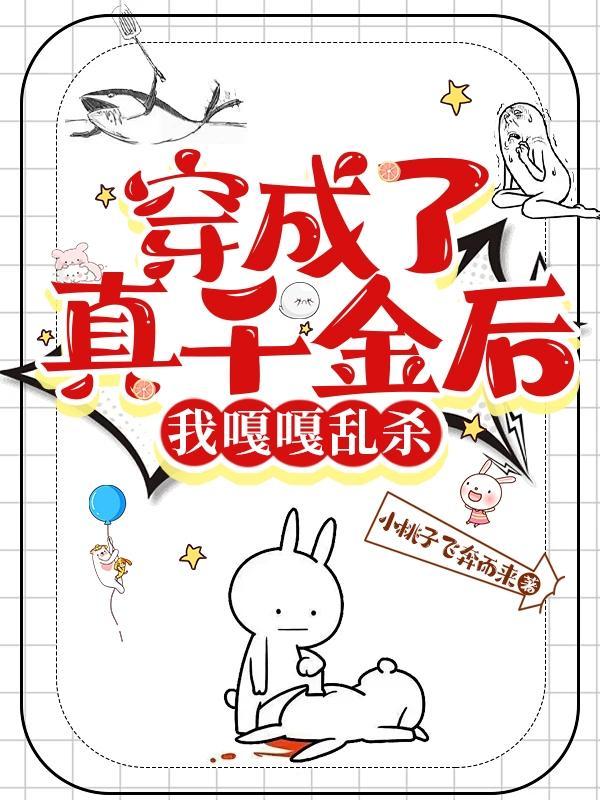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放开为师漫画 > 第85章 师尊真的生气了89第一更(第2页)
第85章 师尊真的生气了89第一更(第2页)
景松哀哀唤道,“弟子知错了……”
“玉师叔,景小师弟又怎么招惹您了,竟能惹得您动这么大的气?”
木月白无奈,站起身绕过景松进屋,“晚辈还是先帮您看看吧,气大伤身。”
殷柳瞥向景松,忍不住嘲讽一笑,“师尊终于收拾你了,景师弟你好自为之吧。”
屋里,玉沉璧面色白,一副病恹恹的模样靠在床头。
“心火燥郁,脉象紊乱。”
木月白帮玉沉璧把过脉,有些惊奇:“玉师叔,您这心病怎么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玉沉面色不虞,心头憋着一口气道:“严重就严重吧,我不治了。”
“我不是告知景师兄要多亲近您吗?”
木月白疑惑,“是景师弟忘了?”
玉沉璧的脸色更难看,“不必提他!”
木月白隐隐猜到些什么,试探提问:“玉师叔您不愿意,是不是觉得景小师弟冒犯了您?”
“……”
玉沉璧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同样都是男子,玉师叔您有什么可害羞的?讳疾忌医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木月白啼笑皆非,苦口婆心的劝:“晚辈明白您拉不下面子,但是治病要紧,景小师弟受累还没觉得您麻烦,您就别端着了。”
玉沉璧语气不善,“那小子心术不正,我留他不得了。”
“心术不正?能有多心术不正?”
木月白并未放在心上,随口开玩笑道:
“总不能是景小师弟与您亲近的过程产生了感情,想为您的以后负责吧?”
“……”
玉沉璧的脸色更沉了。
然后又听木月白自我否定:“这根本不可能,您平日对待景小师弟这般严厉,稍有不顺便是非打即骂,景小师弟真是眼瞎了才会看上您。”
玉沉璧十分赞同,“我也是这么觉得,景松应该不会眼瞎。”
“景师弟伤成那样,应该是您打的吧?玉师叔,您冤枉景师弟了。”
“我没冤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