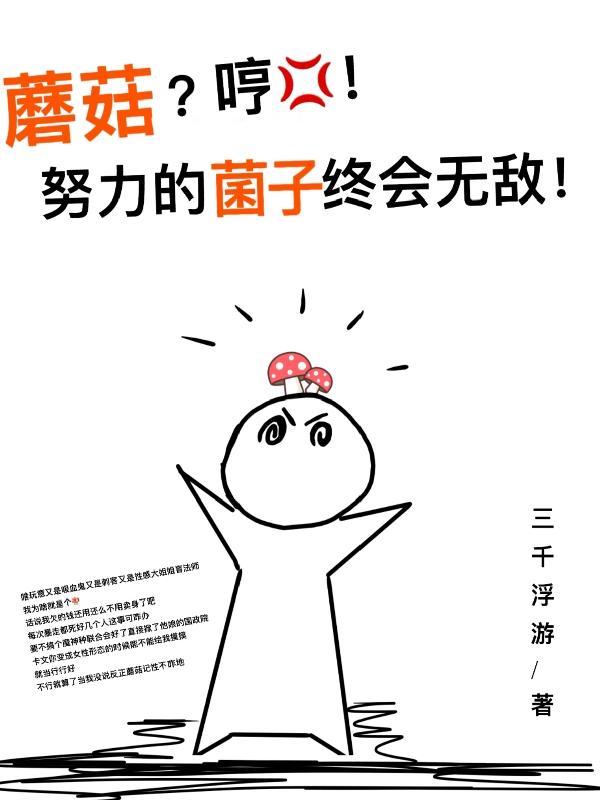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上头了前任综艺全集免费观看 > 26(第1页)
26(第1页)
一进门还没有空调,一个巴掌大的小电扇在头顶上嗡嗡的转悠。
没有人能陪李恩年考试,天南海北也都是李恩年自己跑。
那个时候网上订票还不普及,李恩年在南方的几个地区考完,还要赶着回家订票,重新准备。
他并不想回家见李学海,去呼吸那个房间里乌烟瘴气的空气。
平时他会去找孔源或者宋鹤一,但现在这俩人都知道他去考试。
一来还没考完,他也不好意思去惹人牵挂。二来家里有琴,他可以再多练练。
李恩年一年多都不怎么回家,李学海也没见打过一个电话。
冷不丁一回家,李学海先当着一帮人的面骂起了李恩年。
“小兔崽子你又去哪鬼混了?”
李学海喝酒了,但是没醉,他就是习惯性的骂李恩年两句,仗着酒势骂的更起劲,“是不是你妈又偷摸给你钱了?”
李学海有那种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认为全家的钱都是他给的,都是伸手朝上管他要钱的。
席雅娟挣多少在他那都是没挣,花的钱都是他的。
席雅娟不和李学海离婚,有一方面也是因为李恩年学钢琴的负担太大。
席雅娟一个人供李恩年学钢琴有点费劲,李学海拿得再少也能让她在日常生活花销上节省一些。
但李学海又是穷怕了的,他买着比席雅娟还多的衣服鞋子,却总用自己过去的时候和李恩年比。
他觉得自己对李恩年好的要死,动不动就说:“你比我们小时候好多了,我供你念书你还想怎么样?”
李恩年有时候真想一书包抡过去说他不念了。
李学海像个守财奴一样扣扣搜搜守着他后半生踩了狗屎运的来的钱,又不肯让李恩年躺平。总做着给李恩年一口饭吃就能飞黄腾达的春秋大梦,期盼着他的劣质基因在遗传的过程中产生一次不可能的突变。
李恩年早就习惯了李学海自以为是又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懒得争辩,低头含糊地应了一声,就回房练琴了。
集训的地方琴房不好抢,隔音墙听的耳朵也痛,原本他计划在家待两天再练一练,就回北京考试。
但是李学海一天都忍不了。
原本李学海对于李恩年没事在家弹一弹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极大的满足了他在亲戚面前装逼的面子,尽管他从来不支持李恩年学琴。
但这次李学海不知道怎么了,一听见李恩年弹琴就跟触发了什么开关一样,暴怒着一脚踢开门。在李恩年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抄起一把椅子一下锤在琴上,还有李恩年的左手上。
“嗡”
的一声,钢琴和李恩年的大脑都在一瞬间不堪重负地发出了哀嚎。
李恩年捂着手直接跪在了地上。
他甚至感觉不出来很分明的疼痛,麻木和酸胀充满了他整个手臂,过了好久他才反应过来,他的手被砸了。
李恩年疼得有点发懵,呼吸都有点调不过来。
他听见李学海在骂他:“都他妈高三了,你还练你那个破琴!你练琴能当省长吗?你能当大官养我吗?”
李学海做梦都想当官,当大官。不只是想要钱,还想要权力,像使唤李恩年那样对手下的人吆五喝六。
所以他也望子成龙望得要疯了,他想让李恩年当官,他好出去狐假虎威的作威作福,夸耀他自己的基因多牛逼,能生出个这么厉害的儿子来。
李恩年琴练的好是多亏他,李恩年学习成绩好也是多亏他。
李恩年考上八中的时候李学海不知道跟亲戚吹了多久,只有李恩年自己知道自己为了拉平他那个半身不遂的数学,他努力把英语和语文提的比别人高出了多少分。
包括这次李恩年时常不回家,李学海不来问他,一是因为李学海懒得管他,二是因为宋鹤一给他补了数学,让李恩年的成绩好了不少。
“你别他妈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你妈在盘算什么?”
李学海指着李恩年的鼻子骂道,“就你还想考艺考?你们娘俩拿他妈我的钱去败活!”
李恩年痛的要死,气的也发疯,疼的蜷缩在地上,抬起头狠狠地瞪着李学海:“我学琴你没给我掏过一分钱,别往自己脸上……”
李学海一脚就踹了过去。
高中之后李恩年的个子长高了,李学海不敢这么揍他了。
也不知道是一直忍着还是现在终于看到了李恩年疼的起不来,李学海终于抓住了机会又上去补了一脚:“别他妈那么我看着我,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不服你就去报警,我他妈是你亲爹,是你直系三代亲属,我进局子了你这辈子都别想好过。”
李恩年疼得缓不过来,咬牙切齿地看着李学海,骂过的所有脏话在李学海这句亲爹面前都显得格外无力。
李学海像终于抓住了李恩年的痛点似的,大摇大摆地从李恩年包里掏出车票,得意洋洋地撕了个粉碎,“正好,你左手坏了,就别去考了。不过右手没坏,高考还是能考的。”
被砸懵的李恩年这才反应过来,李学海就是故意的,从刚开始就是故意的,就是不想让他去考。
席雅娟家里没什么亲人,孤苦无依地嫁给了李学海,娘家没人能给撑腰。
李恩年很少把他和李学海的矛盾告诉席雅娟,这可能也是宋鹤一对施强的无奈,告诉了能怎么样。
以前的事只要不过分李恩年,能忍的时候也就忍了,他身为儿子的总不能撺掇父母离婚,不然会被人戳脊梁骨骂白眼狼。
但矛盾会积少成多,人也会蹬鼻子上脸,在一次又一次的容忍和无视中,矛盾终于到了不能忍的地步。
李恩年已经是一个将近十八岁的成年人了,年轻的男生生气起来力大的十头骡子都拉不住。李恩年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站起来的,他只记得他看着李学海那张令人生厌且扭曲的脸,用还没受伤的右手抄起李学海拎进来的那把椅子砸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