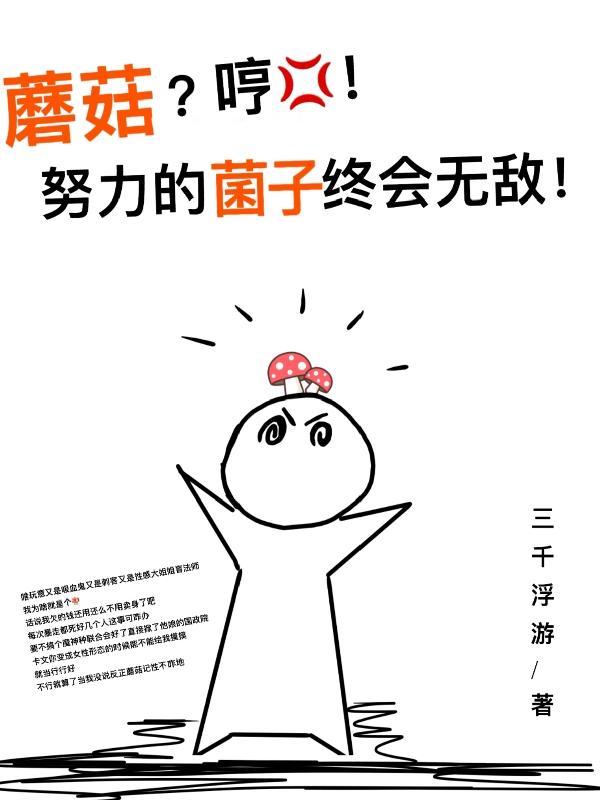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古代社恐的人 > 第75页(第2页)
第75页(第2页)
李枳:“说得好像你哪回来不带东西一样。”
顾池从油绸里拿出球灯笼和月饼,见李枳不过来,他就自己走了过去。
离得越近,他越没法把自己的眼睛从李枳身上挪开,见李枳拿着球灯笼摆弄,心情似乎变得好了些。
烛灯下那双他知道有多软嫩的唇吐露出熟悉的埋怨:“都说了,我不是孩子。”
别总拿孩子的东西哄我。
顾池问她:“喜欢吗?”
不管是不是孩子的东西,你喜欢吗?你会因为收到这个,而感到高兴吗?
李枳第一次听顾池这样问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违心撒谎,说:“喜欢。”
顾池低头触碰她的唇,像是要把那一声来自李枳的“喜欢”
吃进肚子里。
李枳顿了一下,她知道自己应该推开顾池,可是……
为什么要推开呢,反正她又生不了,且早已不是完璧之身,她为什么要怕,为什么不能……不能放纵一次,让自己也快活一回。
这次,她被亲得腿都软了也没把人推开,反倒是顾池,似乎察觉到了她的异样,停下问她“怎么了”
。
李枳轻轻喘着,也不说话,就这么看着他,看得他无力招架,又低头含住了她的唇
李枳站不住了就伸手去抓顾池的衣服,在顾池托住她时不再压抑喉间的呜咽,因为实在受不住,眼角都沁出了泪。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坐到了床上,衣服一件接一件地往床褥上落,落到后头李枳在雨夜的寒凉下带着哭腔喊冷,顾池便用自己的身子去暖她,暖得彼此大汗淋漓也不见分开,反而越缠越紧密,由着陈旧的床架子在雨声的遮掩下吱呀作响了一晚。
……
第二日风停雨歇,窗外映着暗蓝色的光,是天还没大亮的早晨,洗得发白的旧床幔将床内床外分割成了两个世界。
床外是简朴的庵庙住房,一应家具都很老旧,唯一色彩鲜艳一些的,便是门边那两盆菊花。
床内,柔软的身躯被结实健壮的双臂紧紧抱着,肌肤相贴,发丝纠缠,说不清的旖旎缱绻。
顾池没睡,李枳也没睡,虽然她很累很累,累得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了,可就是睡不着,每次闭一会儿眼睛就睁开。
李枳嫌顾池身上太热,稍微往后让了让,那温度立马又跟了上来,像只缠人的小狗,一刻都摆脱不开。
李枳想说时间不早了,让他快些离开。
不曾想顾池比她先开口,说出那句不知道提了多少次的话语:“琼实,嫁给我吧。”
昨夜温存时,顾池让李枳唤他阿池,李枳便也说了自己的表字。
李枳静默片刻,用夜里哭哑的声音回他:“你该走了。”
顾池没想到李枳这样无情,天亮之前还在抵死缠绵,天亮之后就能把他赶下床,还要他忘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快些离开。
顾池无法,穿上衣服又收拾了一下屋子,告诉李枳自己要去趟安州,十一月回来。
床上,李枳轻轻地“嗯”
了一声。
顾池从窗户那翻了出去,不过他没走。
庵里有早课,李枳没去一定会有人来问,他听李枳对来问她的人说自己病了,那人不曾起疑,也知道李枳这有药,还替她拿了煎药的炉子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