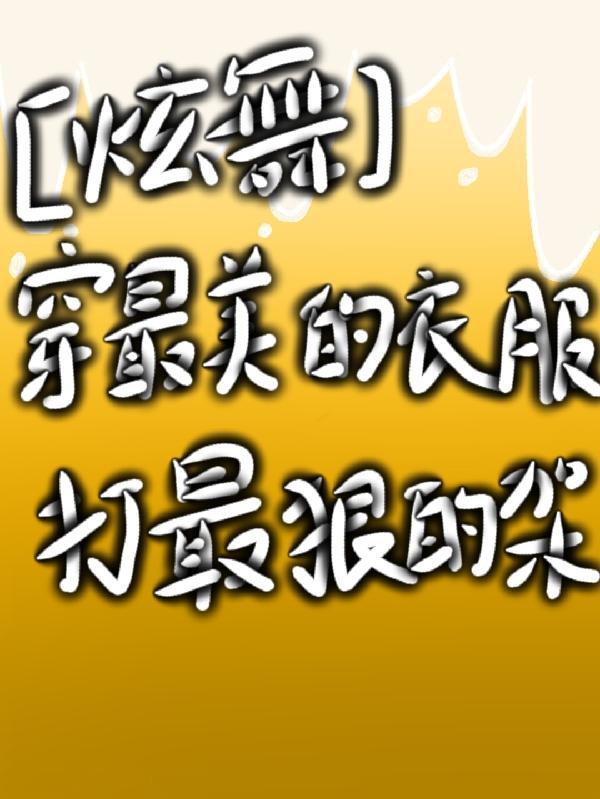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开局觉醒女帝之魂 > 第60章 第 60 章(第1页)
第60章 第 60 章(第1页)
燕家如今已然是强弩之末,对邬宁威胁不大,真正令邬宁忌惮的是儋州藩王,她的嫡亲皇叔邬复。
儋州与霖京相隔五千里,位处四季如春的南方,虽是边远之地,但紧挨着一望无际的南海,周遭并无战乱纷扰,其富饶繁华毫不逊色霖京,且邬复麾下兵强马壮,实力强劲,在众多藩王中屈一指,说是晋朝的土皇帝也不为过。
邬复本身很满足于现状,乐得做一个有实无名的土皇帝,只要晋朝仍为邬氏天下,只要朝廷不提削藩二字,他的兵马绝不会踏出儋州半步,也绝不会允许其他藩王在九州作乱。
这原本是邬承登基那年所布下的一盘棋局,他将自己的亲弟弟送往五千里外的儋州,一则可以避免因皇位争斗兄弟残杀,二则可以制衡那些野心勃勃的九州藩王。
而几十年来,亦如邬承所愿,纵使晋朝天灾不断,前有妖后祸国,后有权臣持政,也并无哪个藩王敢顶着一南一北两座大山举旗生事。
只可惜,邬承千算万算,没算到邬复养出了一个好儿子,更没算到邬复会在燕氏之乱爆时病故身亡。
邬复的死没有给儋州局势带来半点影响,其长子邬擎承袭了王位,轻易接手了父亲的旧部,成了儋州新一任的土皇帝,反观朝廷这边,如同一团乱麻。
对比之余,邬擎自然心有不甘,他也是高贵的皇族血脉,他比邬宁更有帝王之才,这晋朝的江山不该交付于一个只能充作傀儡的小姑娘手中。
而邬擎的野心得到了邬复旧部的一致认可。
没有人愿意甘居一隅之地,都想着夺得天下,都期盼着名垂千史。
儋州一动,九州便跟着乱了。
邬宁有一段时间其实挺想不通的,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到底管她什么事难道是她想打仗吗难道是她想扩张势力吗她就是想平平淡淡的在宫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而已,古往今来多少皇帝不都是像她这样过日子的,她究竟招谁惹谁了,不仅要遭世人唾弃,还要时刻把脑袋扎在裤腰上。
后来才想明白。
换做别的皇帝,世人会体谅“他”
年幼登基,接下外戚掌权的烂摊子,又逢藩王作乱,如此内忧外患,四面楚歌,受不住江山也在所难免,可她,邬宁,世人口中的长乐女帝,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子。
女子为帝,便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
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只要能坐稳皇位,平定九州,莫说这般伏低做小的哄着慕徐行了,若给慕徐行生个孩子能换他死心塌地,邬宁也是愿意的。
当然,眼下还不至于。
毕竟慕徐行真挺好哄的。
“你这字写得是越来越有风骨了。”
“有吗”
“有啊。”
邬宁双肘撑着书案,笑着恭维他“兴许再过些时日,你就成书法大家了。”
慕徐行不擅文墨,却懂得品鉴,知道自己这几笔字撑死了算刚入门,听邬宁这么说,不禁面颊热,只将镇纸挪开,铺了一幅画遮盖。
“咦”
邬宁的注意力被画吸引“这是什么”
“这是”
慕徐行犹豫了一会,红着脸说“女子的月事带。”
邬宁一愣。
她上辈子用过华氏商铺的月事带,慕徐行这么一说,她再看这幅画,倒是有点那个意思了。
“我见陛下每次来月事,都不大方便,所以”
“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慕徐行立即正色,他打开书案旁的樟木箱子,取出几团松软雪白的棉花,那棉花一经拉扯,便像蛛网似的舒展开,慕徐行小心翼翼的将其铺在布满针尖的木板上,一层又一层,铺了大约七八层的样子,紧接着又取出一块同样布满针尖的木板。
就看他鼓捣来鼓捣去,一炷香的功夫,几层棉花就变成了一张轻薄柔软的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