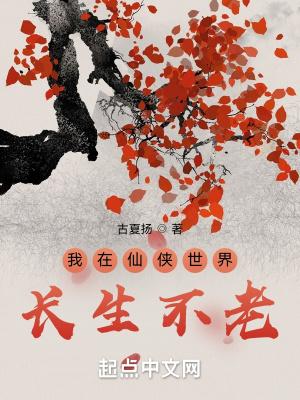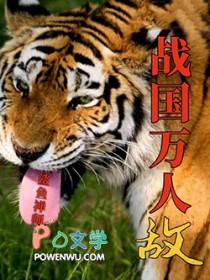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起点文女帝觉醒后TXT > 第96章 第96章(第2页)
第96章 第96章(第2页)
能说什么呢,明知不会出事,明明有人搜寻,邬宁偏要冒着大雨与禁军一同进山。
沈应紧抿着唇,用袖口蹭掉脸上的雨水,将油纸伞朝着邬宁的那边稍稍倾斜。
邬宁跟着上了山,禁军不敢不尽力,一块草稞子都不放过,几乎是一寸寸的往林子里摸,如同在间篦跳蚤的篦子。只碍于这场劈头盖脸的大雨,效率很是缓慢。
幸而是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黑漆漆的乌云逐渐积压在北方的地平线上,山林正上空的云色便浅淡了,雨势也跟着平息,一道彩虹悄然挂在了天边。美则美矣,无人欣赏。
雨都停了,人还没找到,禁军统领回头看了眼邬宁的脸色,开始不由自主的打冷颤。
邬宁脸色极差,苍白的像是一片冰雪,眼睫垂下来,遮住一半的瞳孔,剩下的一半,黑是黑,白是白,透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邬宁第一次流露出这样的神情,令人心惊胆颤的神情。
禁军统领仿佛被她掐住了喉咙,有些喘不过气。
谁也不知道那时的邬宁在想什么,甚至连邬宁自己都不清楚,她脑子里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念头:倘若慕徐行有个好歹,这天底下就再没有能跟她说话的人了。
不成立的因果关系,不切实际的结论,让邬宁隐隐感到万念俱灰,但在当时神思混沌的情形下,很多东西转瞬即逝,唯有一声“找到了”
清晰明确的扎进邬宁心口。
“找到了!陛下!常君找到了!”
邬宁睁开了眼睛,仍然黑白分明,却像乌云逐渐褪去后,天际边那一小片湛蓝如洗的晴空,干干净净的,清透明亮。
“人呢?人在哪?”
“陛下不必担忧,常君并无大碍,只是不慎崴了脚。”
沈应望着长舒了一口气的邬宁,扭过头问:“常君可有淋雨?”
“常君便是躲雨的时候崴到了脚。”
“可有伤到筋骨?”
“这一时还瞧不出,要等医官验过才知。”
沈应暗暗翻了个白眼,觉得这报信的当真蠢笨,打一棒子答一句。
好在该说的都说清楚了:“陛下,既然常君无碍,咱们就先回去吧,回去换身衣裳。”
沈应有自己的小心思,他不愿慕徐行看到邬宁这般狼狈的模样。
邬宁瞥了眼身上肮脏的泥点子,微微颔,转身下了山。
没过多久,慕徐行被徐山搀扶着,一瘸一拐的回了营帐,这时邬宁已经换了衣裳,站在营帐外的空地等着烤鹿肉,那一团赤红的火焰映照在她脸上,仿佛是黄昏的霞光。
而慕徐行又是另一幅光景,他身上滴滴答答的流淌着雨水,好像怎么都流不完,好像头顶还有一片云雨,他一条手臂搭着徐山的肩膀,左脚不能结结实实的落地,至多蜻蜓点水似的支撑一下,右脚紧忙往前一蹦,凄惨中又掺杂着些许滑稽。
邬宁看着慕徐行,慕徐行同样看向她,本就不灵活的脚步也停住了。
这相距遥远的对视让沈应心中一惊,不假思索的挡在了邬宁身前:“陛下……”
“你别太得寸进尺。”
邬宁轻描淡写的说完,目光再度落到火焰上,没有继续盯着慕徐行看。
沈应回头,见慕徐行已经被徐山搀扶着进了营帐,不由轻舒了口气,紧接着心中涌现出一阵阵的失落和空虚。
他今日的确是得寸进尺。
就一日,他想独占邬宁。
沈应永远记得当年那场马球会,邬宁身着一袭红色骑装,高居骏马之上,用鞭子戳了一下他的背,他转过身的瞬间,便在心底埋下一个梦。
和邬宁一起骑马打猎,炙鹿肉,饮美酒,共赏夜晚的篝火与繁星,这是他少年时日日期盼的梦。
可惜梦与现实相差甚远。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自己,换来的只是一场浮华。&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