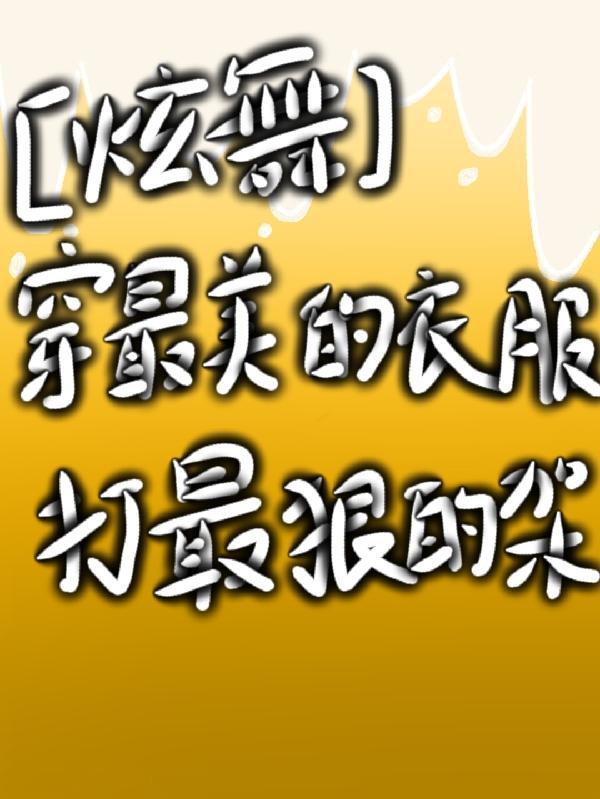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等你宛在水中央下一句怎么接 > Ch 47(第1页)
Ch 47(第1页)
离开饭堂的人找了一圈在东院泳池旁看见抱膝而坐的孟以栖,也不晓得她是不是故意为之,明明有很多地方能躲起来哭,却偏偏选在他的地盘发泄,以至于有人的心更加塌陷了,不听使唤地走向还在掉眼泪的人。
“你再往前栽进池子里,我可不救你了。”
还在抽噎的人抬头望来,因着心里难受至极,回话也含着怨气,“我会游泳,谁要你救?”
“嘴巴不是挺会咄咄逼人?”
杨靖安弯腰来看她泪痕遍布的脸,“怎么先前不据理力争?”
“有什么用?你那个亲戚母女两人一个比一个会卖惨,连我爸爸妈妈都向着她们,我哪里是她们的对手?”
只有忍气吞声的份!
“这就是你跑出来的理由?”
有人伤心死了,也忘了与某人尴尬的处境,哭得稀里哗啦地问他,“我要怎么解释,我爸妈才会相信我呢?”
“你不用解释了。”
“被误会的人又不是你!”
孟以栖不听劝地还在掉泪眼。
“哪有父母不向着孩子的道理?孟以栖,你信不信回去之后,你爸爸妈妈会跟你道歉的。”
哭断声的人眨着疑惑的眼睛来问他,“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错。”
孟以栖终于不再哭了,因着饭堂里她觉得一向对自己深信无疑的父母都选择站在另一头,还有谁会无条件地相信她呢?总不可能是与自己老死不相往来的杨靖安,可他此刻里却冰释前嫌地选择相信自己。
弯着腰的杨靖安叫她一错不错的眼神盯得心口倏然收紧,呼吸一热地直起身来催促她,“进去洗把脸,哭得丑死了。”
孟以栖抹着鼻涕眼泪起身,嘴里小声地嘀咕不满,“我要是丑你也没好到哪里去。”
“我听得见。”
有人警告她。
反正她装作没听见,熟门熟路走进洋楼里找卫生间,等洗完脸收拾好出来,陈妈的儿子王南柯拎来了两份食盒,里头是刚出锅不久的牛肉汤面。
“愣什么?”
打发走王南柯的杨靖安率先坐进餐桌里准备吃面,“你不会被气饱了吧?”
怎么可能?席上心不在焉的那阵子根本没吃多少东西,孟以栖立马朝餐桌走来,“是啊,我气得能吃下一头牛!”
抄起筷子的孟以栖吃得正香之际,越来越沉默的气氛却令她心生愧疚之意,要晓得在凉亭里撞见阔别已久的杨靖安时,她想得可是坐实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约定,可眼下她与他却和睦地坐在东院里头吃面条。
“杨靖安,”
孟以栖咬断面,终于肯来问他,“你在国外念书这段时间顺利吗?”
“你原来晓得我出国念书了?”
某人讥讽她这段时间里的无声无息。
孟以栖当然也心有不畅快,但想想何必呢?他出国与否都是个人事件,合该没理由告知她一声,更遑论已经闹掰的情况下。
“不是你说的老死不相往来吗?”
“我说了很多话,可你记在心里实现的只有这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
讨厌被误会的人张嘴就来反驳,“明明是你一走了之后开始失联。”
我只是被动地与你断绝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