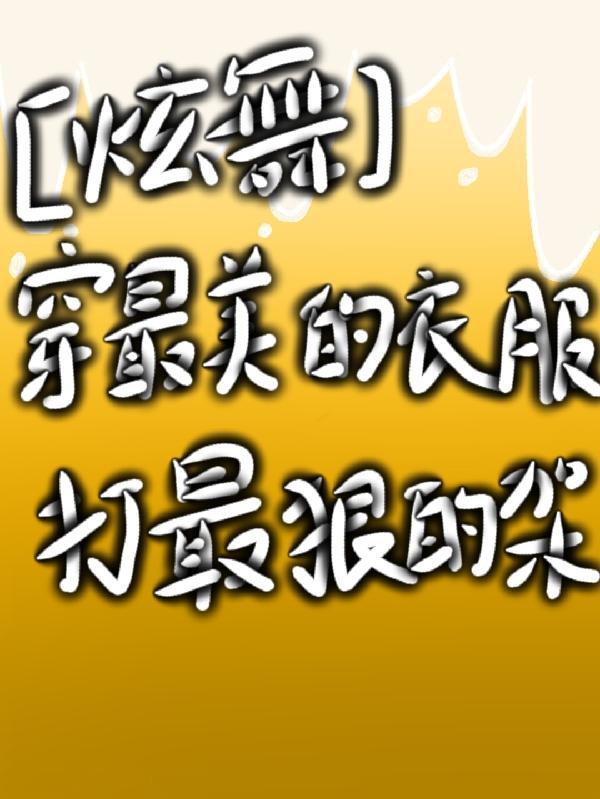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70年代的图片 > 第21章(第1页)
第21章(第1页)
居委大妈催了两声,杨廷薇噢噢应着,趁他们研究厅里那张八仙桌的材质时,飞快地掀起块地板,把刚才写的纸条塞进去。这是沈根根教她的,万一有事留张条在家,他会想办法救她。她的心提在嗓子眼,低头装作系鞋带,借眼角余光看了看外面,幸好他们又在看院里的铁树,还一个个啧啧称奇,齐屋高的铁树比较少见。
杨廷薇收下挂在小天井檐下的篮子,里面是浅浅一层栗子。她统统倒进手帕,放在包的外层,然后锁好门,跟着来人回了西乡。
住过的地方已经有新人,队里重新分配给杨廷薇一间小屋。真的小,除了床之外只放得下两张凳子,带她过来的妇女主任皱了皱眉,“先住着吧,以后有地方空出来就把你挪过去。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把旧时代娇小姐的习气全都洗掉,明白吗?”
杨廷薇低头摸着辫子不说话,妇女主任以为自己的严辞厉色镇住了对方,又补了几句,无非是要她向姐姐学习扎根农村,争取做个铁姑娘。
晚上等狗都不叫了的时候,杨廷薇拎起没打开过的包,悄无声息地走了。
还是沈根根教她的。要是他们抓她回来,别跟他们当面闹翻;瞅空跑上海去,别坐车别乘船,沿铁路线走;躲起来等他想办法,如今的世界正在天翻地覆,谁都不知道明天的事。
没人发现她的出走。
杨廷薇庆幸那间小屋住不下第二个人,让她能够顺利脱身。
在村口杨廷薇辨了下方向,收回视线时才发现不知何时身后跟了两条野狗。她走,它们也走,她停,它们也停。它们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着碧荧荧的光,她俯身装作捡石头,同时发出霍霍的驱赶声,却没起作用。两条狗后退几步,以令人害怕的冷静打量着她。
杨廷薇咬住下唇看着它们,只能继续走自己的路,她越走越快。等那两条狗终于不见时,杨廷薇发现鞋也丢了一只,袜子被霜打湿,和脚板同样冰冷。她没敢休息,换上包里的棉鞋向东走。
直到天空出现启明星,杨廷薇才长长呼出口气。
没走错方向。
她笑了笑,可这笑意像冰葫芦外面的糖,在冻僵的脸上挂不住。
从梅城到上海,她沿着铁路线远远绕开了人住的地方,直走了三天三夜才到。
秦梅宝在街道排队买豆浆油条,看见有个人走走停停。那人像是他乡下的二姐,头发乱蓬蓬的,脚上的鞋张大了嘴,拎着只行李包,上面有“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的字样。
二姐在每个门牌号前发会呆,然后往前走,眼看越走越远。
秦梅宝低下头,他穿的是黑色灯芯绒面的棉鞋,针脚细致,布鞋底下面还有层塑胶底。这是大姐去年的手工活。
杨廷薇没来过这里,也不记得具体地址了。她越想记起来越记不起,似乎姐姐说过巷口有个挺大的垃圾箱。可是,所有的巷口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样子。
“杨廷薇?”
有人叫,杨廷薇吓得一哆嗦,完了,被抓住了,跑不掉了。
“杨廷薇!”
少年的声音带着几分不耐烦。
杨廷薇慢慢回过身,没有追兵,后面只有一个少年,和她一式一样的眼睛鼻子。
她认出来了,“梅宝!”
“老头老脑,”
杨廷薇拍着胸口,“叫我二姐。”
她注意到秦梅宝手里的竹篮,篮底垫了张纸,但篮子仍然是浸饱油的暗色,“买早饭?”
她咽了口口水。
“嗯。”
杨廷薇大口喝着豆浆,同时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太大的吞咽声。秦伊恬却没像过去那样管束女儿的吃相,只是说吃吧多吃点。
等秦伊恬上班去了,杨廷薇问秦梅宝哪里有浴室。
秦梅宝警惕地说,“我没钱。”
杨廷薇弯起手指在他额头轻轻敲了下,“小鬼头,我请你。”
等秦伊恬下班,杨廷薇已经做好晚饭,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看着女儿期待的目光,她勉强笑了下,“这么能干了啊,薇薇。”
杨廷薇边帮母亲舀饭,边得意地说,“除了做饭我还会绣花糊纸盒腌酱菜,还可以到人家去做帮工。妈妈你放心,我不做吃白饭的人。”
米是江西来的籼米,煮后又干又黄,嚼在嘴里没半点糯性,秦伊恬舀了勺汤,略微咸了点。杨廷薇出生时,杨鸿生和她都以为后面不会再有孩子了,对最小的总是有些偏心,因此薇薇始终没有榕榕能干。
杨廷薇往自己饭里舀了几勺汤,吃了口一吐舌头,“打翻盐罐头了!”
她笑道,“在酱菜厂做惯了大袋倒盐的活,手收不住了。”
秦伊恬问,“你上班了?”
杨廷薇点头,“没有正式给我安排工作,我打的是零工。”
她叹口气,“书也没得念,工作也没有,…”
她突然醒悟到不能往下说了,自己和母亲没提不想插队,只说父亲进农场后家里没人,想妈妈了,所以来住阵子。
大儿子大女儿长相像杨鸿生,二女儿小儿子像自己多些,灯光下看杨廷薇,就像看年轻时的自己。大姑娘了,长眉大眼,菱形嘴,尖俏的下巴。秦伊恬出了会神,直到秦梅宝打断她的思绪,“妈妈,我和同学晚上有事,我走了。”
秦伊恬胡乱点了两下头。
关门的声音传上来,饭桌上母女俩突然都沉默了。好久秦伊恬才说,“你还是回去吧。”
杨廷薇一口饭哽在喉咙里,上不上,下不下。嗓子眼特别痒,万一饭粒咳得到处都是就麻烦了,她连忙用手捂住嘴,想硬生生地把那口饭咽下去。她做到了,饭粒擦过咽喉,被强压进了肚,留下丝丝麻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