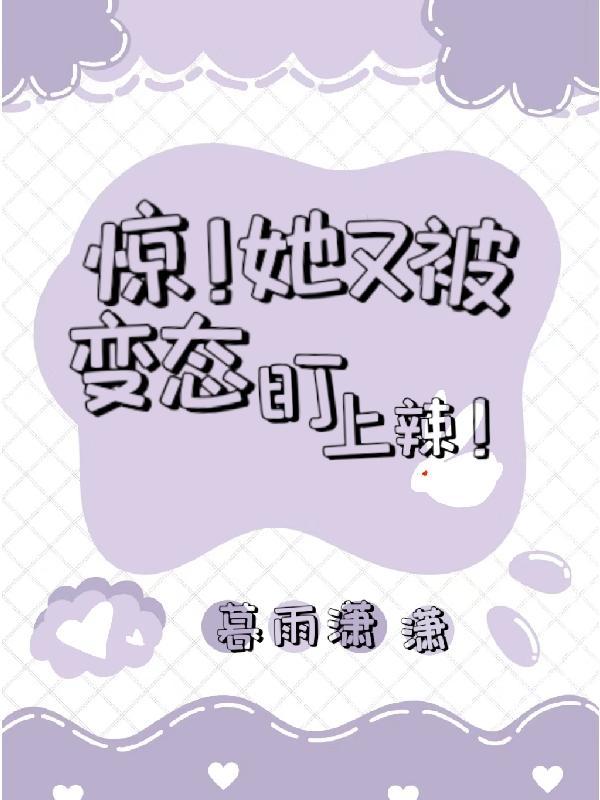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快穿之我渣遍了全世界 > 第 521 章 想安享晚年的每一天34(第1页)
第 521 章 想安享晚年的每一天34(第1页)
…
深夜,江无错不放心,一进陆遂的房间,就闻到浓郁的血腥味。
冲过去一看,女人泡在浴桶中,水已经被血液染的赤红。
热水腾腾热气氤氲而上,在陆遂发梢凝成几滴水珠,将落未落。
他坐在地上,松松垮垮穿着里衣,目光落在地面,又好像涣散失神,什么也没在看,一只手浸没在水中,丝丝缕缕血液如无数触手般朝四周蔓延扩散。
“您疯了吗?!”
江无错跑过去,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纱布,掐住血管,捆住被陆遂割出四五道口子的手掌。
他真是……
江无错妥协道:“您非要做,也不一定要用自己的血啊,您让我说些什么好!”
陆遂坐在地板上,低着头:“我不想让她身体里流别人的血。”
江无错看了看泡在血水里毫无变化的尸体,重重叹气:“那好,让她好好泡一泡,我们先把伤口处理一下,然后睡一觉,行不行?说不定明天就能见到活生生的人了。”
幽幽灯光下,血腥味呛得人嗓子发腻,像是有了实质,一缕缕在空中延伸着,包裹着一切有形体的物什。
在绵软的哄劝中,陆遂却摇了摇头,看向女人浸没在水中的伤口。
“别管我了。”
江无错一听这种倔话,眉头就忍不住直突突,满是薄茧的大手一把掐住他的后脖颈,把他的脸扳正过来:“别管你?”
“我不管你谁还管你?那你就这样流血吧,不管你了,流死了
更好,等这女人醒了我就给她送回将军府。”
他好像也在相信着她会活,只是一个态度,也足够让陆遂亮起雾蒙蒙的双眼。
有了慰藉后,徐徐升起的是对这番话的气愤。
“不行!”
陆遂梗着脖子,憋起一口闷气,一把反握住江无错的手腕,大声喊了一句。
“不行?小侯爷到时候您都死了,哪轮得到您说行不行?”
江无错阴阳怪气地激将他,手上动作不停,不知怎样发力的,一下子从他手里夺回手腕,将纱布轻轻一抽,打了个不显眼不碍事的结。
陆遂反应过来他是故意说那些,轻轻攥了攥被纱布缠住的手掌,抿了抿唇,低声妥协:“我睡便是,你不要动她。”
“好。”
江无错一直等着陆遂睡熟,才吹了蜡烛,将窗户开了个缝隙后,转身出了房门。
他对守在一旁的侍女隐晦地吩咐:“时时查看着,若是腐烂了,尽量遮掩,提前通知我。”
侍女一想到屋里头那具可怕的尸体,就心头生凉,却不敢多言,点头应了。
…
日上三竿。
教徒一个接一个地被男人从后门带进侯府,黑压压的,聚集在那被半月形荷塘包围的空旷平地上。
面前,有一处双层楼阁。
陆遂似乎刚睡完回笼觉,正倚靠在二楼栏杆处,咬着发带,抬着胳膊扎头发。
一道道痴狂崇拜的眼神从下面投射上来。
他临阵不乱,还慢悠悠地打量着众人。
里面,男女老少,什么样
的人都有,唯一的共同点,似乎是穷。他们身上的黑袍虽然规格一致,料子却比擦地板的巾布还要廉价,细细看去,东一块西一块的黑色补丁。
用发带把头发绑上后,陆遂随手指向一个黑袍人,随后转了个圈,指向天空,一歪头,笑眯眯地。
“我听到了,神说,想要先用你的心脏做个初临仪式。”
被指到的黑袍人大惊:“什么?”
其余崇敬的眼神从陆遂身上挪到黑袍人身上,变得疯狂嗜血。
黑袍人捂着心口,后退着,磕磕绊绊:“不,不,你们别搞错了,祭品不是我们啊!”
其余人怪异地笑着。
“不是我们,是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