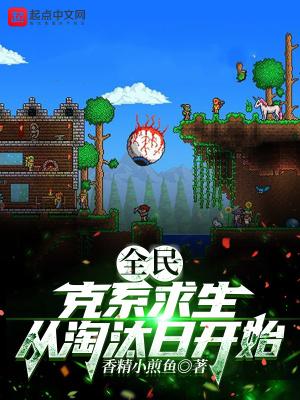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沾洲叹最后和谁在一起了 > 第58章(第2页)
第58章(第2页)
他像个寻常的小孩子缠着母亲,在客栈里要母亲抱着才肯睡觉,那时他并不知道抛弃二字名为何意。
直到第二天被客栈伙计的敲门声吵醒,他在空空荡荡的床上睁眼,耳边是伙计叽叽喳喳但一个字都难以会意的中原话,他痴痴呆呆在被褥上寻找母亲的痕迹,最后被拎起来扔到了客栈外的大街上。
那一年,他四岁。
那条街如飞绝城每一条街般十年如一日的热闹,是这座城中数百条街道里最普通的一处。
他站在这条无名街巷里望着昨日来路的方向,第一次嚎啕大哭起来。
他没有去找母亲,这样的场景过去在他脑中演练了无数次,只是背景从空旷的草原变成了繁华的中原。
可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被放弃了。
长达三年的流浪生活就此开始。
他在数不清的战乱与一次次死里逃生中活成了一只瘦弱却凶猛的小狼。
最后一次他被一支从天而降的飞箭射中胸腔,昏迷在一条水沟里。大概是真的死了吧,所以再醒,活的是第二条命,从一开始就有人捧着饭喂,守在床边,事事以他为先,每晚抱着他睡。
只是有些毛病改不过来,比如不太会笑,不会喊出亲昵的称呼,说不出好听的话。姑且把这些当做第一条命留下的后遗症,好在捡他的那个人并不会因此认为他不配生存。
“我哪都找了,你不在。”
小鱼低着眼睛,快把衣角拧成麻花,“你不要我了。”
小鱼心想,自己不被要是正常的,他总是被丢弃的那一个。可是醉雕呢?祝双衣连醉雕也不要了吗?
接着祝双衣就回来了。
他抬起被泪水打湿成一片的眼睫毛,试试探探看了祝双衣一眼:“你是不是回来找醉雕的?”
“啊?”
祝双衣听得没头没脑,“这都哪跟哪啊?”
他把小鱼搂进自己胸前拍拍背:“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不要醉雕也不会不要你啊。”
旁边柜子轰隆一声,一直藏在衣柜里的醉雕破开柜门跃到地上,走出门槛前冷冷回头瞥了祝双衣一眼。
小鱼在他怀里蹭蹭脑袋,把没干的眼泪蹭干净了,好半天才闷声闷气地问:“那你去哪儿了?”
“我……”
祝双衣眼珠子一转,“我去给你买点早饭。”
小鱼抬头:“为什么不自己做?”
“吃点好的嘛。”
祝双衣确实在来的路上拿最后几个铜板给小鱼买了两块烙饼,正放在家门口的药包上,他想起来,便一边说一边下床去拿,顺道藏起自己的药包,“天天吃我做的,谁受得了。”
小鱼等他走出去了,盘腿坐了片刻,忽然自言自语道:“我受得了。”
祝双衣没有听见。
他拿了烙饼进来,撕开油纸,被香得当即咽了口唾沫,想也没想就咬了一口。
一抬眼,小鱼在床上冷眼看着他。
祝双衣含着烙饼笑得朴实:“我……给你试试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