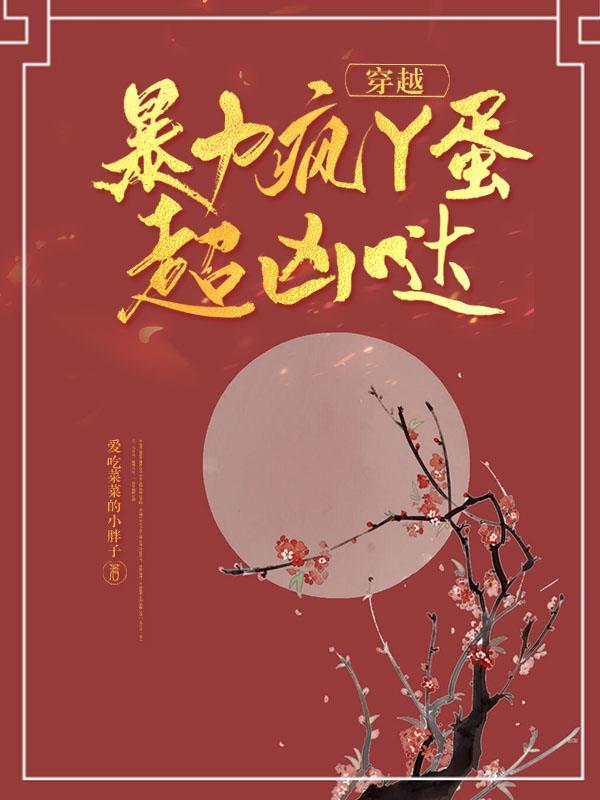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申恩庆依然是你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曹虹又说:这样也可以不耽误葵花结婚,而她又是个好人。你碰上端木林是中六合彩,难道碰上葵花不是中六合彩吗?只有她这样的人你才能把歪歪托付出去是不是?换个人你想都不敢想是不是?也不放心是不是?
曹虹还说:歪歪再好,也有端木林的一半血统,你看他那个样子,还用做dna吗?简直像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两个五仁月饼,当初你要是听我的跟端木林打官司,非让他赔得倾家荡产不可。现在不扯那么远了,可你也犯不着那么死心眼,你懂我的意思吗?管静竹茫然地看着曹虹,曹虹恨不得踢她一脚,还不明白?你为端木林这样的人吃苦受累,不值。管静竹嘴上没说心中却道:可是歪歪毕竟也是我儿子啊,你没孩子,所以你所有的想法都是理论上的。
可是人又怎么可能那么理性地生活呢?她想,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做。
回到家中的管静竹,关起卧室的房门一根接一根地抽了两包烟,她想了三天三夜,没想出任何好办法,而曹虹给她出的主意是唯一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当她再次看到歪歪时不觉泪如泉涌,她知道自己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听到这一决定的葵花倒也并不惊奇,她像老人家那样叹了口气道: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其实我带歪歪也带出感情来了,冷不丁的一走心里也不是滋味。
听到她这么慈悲为怀的一番话,管静竹只觉得双膝发软,就差没扑通一声跪倒,洒泪托孤了。曹虹说得没错,她碰上葵花真是她天大的福气。
歪歪和葵花走的那一天,照例是曹虹把他们送到火车站。是曹虹不让管静竹去的,她说你会受不了,到时候你歇斯底里大发作,又要把歪歪抱回来,人家以为我们在拍戏呢。
他们走后,管静竹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转来转去,心里也像被掏空了一样难以自制。
她坚信她已经疯了,如果她正常,她不但应该去火车站,更应该补一张车票把歪歪和葵花一直送到目的地,看一看生活环境,向葵花的家人交待几句……
她不能再想下去了,慌慌张张地赶到车站。火车已经远去,空荡荡的站台上只有曹虹还在尽职尽责地冲着远方挥手。当她看到管静竹时,真有点儿哭笑不得——管静竹脚上的两只皮鞋,一只黑色,一只啡色。
曹虹再一次抱住管静竹,在她耳边轻轻地说道:静竹,这是天意……你不仅现在不能去,今后永远都不要去……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听鬼的故事吗?最后逃命的人总会听到一句咒语,千万不要回头,否则会没命的……好了静竹,我们回家,时间会洗刷一切的……生活在继续……
管静竹深知曹虹是对的,并且尽到了朋友的心。她能有曹虹这样的朋友也是中六合彩啊!一般的人谁管你这些破事儿?她所在的公司的同事,一直都以为她过得很安稳很幸福,甚至还很羡慕她,压根儿不知道她有一个负心的老公和一个哑傻的儿子。她像钟摆一样扮演着双重的角色,这种平衡也来自曹虹的友谊。
什么叫大恩不言谢?
可是她依然泪流满面。
一时间,她变成了孤魂野鬼,出出进进都是一个人,却已经完全不适应安逸舒适、了无牵挂的日子了。
三
屋里落了薄薄的一层灰,灯光还是那么幽暗,他醒过神来,到家了。
这回他花了两周的时间陪一个客人去马尔代夫群岛旅游,十多天换了七八家超豪华酒店。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冷不丁回到家中,才意识到旅途中的奢华与梦幻。
在选择客人方面他是很谨慎的,他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做的,反正他不能落到要报复全世界男人的女魔头手里。
这一次他的客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寂寞女人,先生冷落她多少年了,她郁闷得不能自制,便到外面去散散心。如果说她有什么怪癖的话,便是她手不离电话。她一共有三个手机,来回不停地打,总是低声地诉说,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便构成她生活的全部。
后来她给他买了一个8000多块钱的新手机,当然是在报酬之外的。只是他们从来不交流,也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他不过是她新买的一只路易威登的手袋,用过几次之后是一定会厌烦的。
房东的儿子叫王植树,据说是植树节那天生的。现在王植树又在扯着嗓子喊“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
,这首《血染的风采》他只会唱这一句,所以他就来回地唱,无论他怎么声嘶力竭都没有人制止他。他妈妈收租婆明姨自然习以为常,但是邻里街坊为何会如此宽容,还真让人有点儿想不通呢。
他本来是可以换个住处的,但他觉得这儿是他的福地,让他赚到钱,包括植树都有可能是旺他的,所以他不想搬。
他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欣赏着王植树的歌声。他想,什么是悲哀呢?悲哀这两个字对他来说已经太过遥远和陌生。事实上他从12岁开始便失去了这一功能。那一年,他本来富裕的家庭发生了巨变,他至今也搞不清父母亲是跟谁家结了怨,总之他家遭受的是灭门之灾,父母和姐姐全部被杀死在家中,幸亏他贪玩耽搁在了游戏机室一夜未归。
当时他还不太懂事,依稀记得他们家三层别墅的前面,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亲戚,有的见过而有的十分眼生,但人多得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足有五六十人。不光是人多,相互之间还发生了急剧的争吵,吵急了还动粗,甚至大打出手。当然在他们中间,有穿制服的人在维持秩序,劝解拉架。大人们顾不上他,他便拿着一根黄瓜边吃边站在一边看热闹。而围着他家院子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也是来看热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