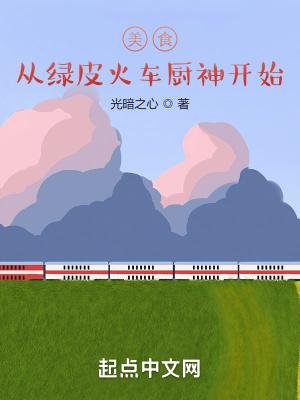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我不曾放纵的青春电视剧演员表 > 第119章(第1页)
第119章(第1页)
刘国志低低地嗯了一声,后来再说什么,望舒就没有听到,她悄悄拿了书包,拉开门走了出去,到了楼外,空洞洞的楼区里只有她的脚步声回响着,从两边人家映出来的灯光那么亮,照得她自己的影子十分孤单。一个人走着走着,心里有点儿难过起来,她掏出手机,一整天第一次不自觉地拨了许承宗的电话,听那边铃铃地响着,他却没有接听。
她看着屏幕,心里有些不安地奇怪,又打过去,他仍然没有接,都这个时间了,他还在忙么?
还是真的生气了,从此不再接听她的电话?
她心里蓦地难过极了,瞪着手机上茫然的小喇叭,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铃铃铃铃。
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她心中一喜,以为是许承宗,接通了就道:“承宗?”
那边的人顿了顿,后来她听见一个很苍老的女人声音道:“是叶望舒么?”
望舒愣了,看了看号码,数字果然很陌生,她嗯了一声,那头的女人轻轻地说道:“我是许承宗的母亲。”
望舒吓了一跳,许承宗的妈?她怎么给自己打电话?
“您找我有事?”
“嗯,请问你明天有事么?”
非常有礼的问话,一如往日在家门口初见许母时她的谈吐一样,只是这时候的声音略显苍老和无力。
“我明天要上课。”
“大概什么时候下课?”
“五点。”
望舒答。
许母嗯了一声,低声道:“我知道了。”
跟望舒道了再见,就挂断了。
望舒拿着手机,有些莫名其妙,她想了想,只得又给许承宗打了电话,那边仍然没有人接听。
她越来越担心,自己没有他别的联系方式,只好不停地打他电话,却—直没有打通。望舒几乎是一夜无眠,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她始终恍恍惚惚的,看见穿着新衣服的蔡茁,勉强想起来两个人昨天去刘国志家里刷墙的事,问她一句:“昨天怎么样?”
蔡茁没回答。
“昨天到底怎样了?”
望舒又问了一句。
蔡茁似乎又是烦恼又是憧憬地叹了口气,“没什么事,他就是一直不停也刷墙,话也不多说一句,看也不肯看我一眼,后来你走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送我回宿舍了。”
她顿了顿,笔尖在本子上用力划了一下,又叹了口气说,“他可真是闷啊!”
望舒看着脸色不佳的蔡茁,想到以往在乡下时,刘国志那拘谨稳重的性格,女孩子喜欢这样闷的男人,注定是要吃很多苦头的,可只要得到了他的心,就一定会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当年往事浮现心头,刘国志在大门口伤心至极下扔掉手机时的样子,清晰如同昨日,望舒心里有些难过,整整一天都若有所失,闷闷不乐。
下午最后一节课上完,她的手机准时响了,看了看是昨天的号码,她心中有些忐忑,想到许母能忍心为了自己脱罪让正当花季的亲生儿子顶下罪名,被判了无期徒刑,她的脊梁上就一阵冰寒。
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她自问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
她接了电话,听见许母道:“叶望舒,到学校门口,王东在那里等你。我想见见你。”
见自己?
“您为什么见我?”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望舒听她说话似乎十分费力,她想拒绝,可最终还是答应了。挂断电话,她跟蔡茁打招呼告辞,蔡茁看望舒要走,心事重重地问她一句:“望舒,你说我喜欢刘国志,是不是错了?”
望舒想了想道:“我不觉得是错,只是你可能要有点儿耐心。他那样的性格,有的时候就算心动了,也会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而把心意堵住,一声不吭很多年。”
从初中到二十六岁,十多年吧,他才回乡下跟自己提亲,实在是个稳妥得近乎呆板的男人了。
“客观原因?”
蔡茁不明白了。
“比如他学历不高,还有年龄差异……”
望舒没有接着说下去,因为蔡茁已经懂了,她愣愣地看着望舒,脸上全是恍然的表情。
望舒对她笑了一下,自己还有事,跟她再见,急匆匆地赶到学校门口,果然见王东站在车旁等着她,望舒对儒雅稳重的王东印象一直十分好,这一次若是别人来接,她是说什么都不敢去见许承宗母亲那样的女人的。她走到王东跟前问:“你知道她找我做什么么?”
“姑姑身体不好,有些话想跟你说,我们上车吧。”
王东拉开车门,望舒坐上去,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就到了医院,她跟在王东身后,乘电梯到了许母的病房,里面光线很暗,正对着落日的窗子被窗帘挡着,只在靠近床头的地方打了几盏小灯,照在雪白的墙上,显得灯下病床上的老人脸色有些灰暗。
许母目光抬起,示意王东出去,等到门在王东身后合上,她看着望舒,轻声道:“你坐。”
声音比电话中听来更为沙哑,但并没有想象中的虚弱。望舒依言坐在窗下的沙发上,看着床上的老人,等着她说话。
许母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无神的眼睛看着病房雪白的天花板,似乎在整理思绪,很久她才说:“那天晚上阿健要杀承宗,听说你跟他在一起?”
“是的。”
“程健是我侄子,为他姑父工作了十多年,最后什么都没得到,他心里是不甘心的。”
望舒没有答话,她静静地坐着,看着许母苍老的脸,想到十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当她杀了自己的情敌,踏在血泊里让亲生儿子顶罪的时候,眼前这个女人的冷酷与狠毒来。
虎毒尚不食子,眼前的女子连动物都不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