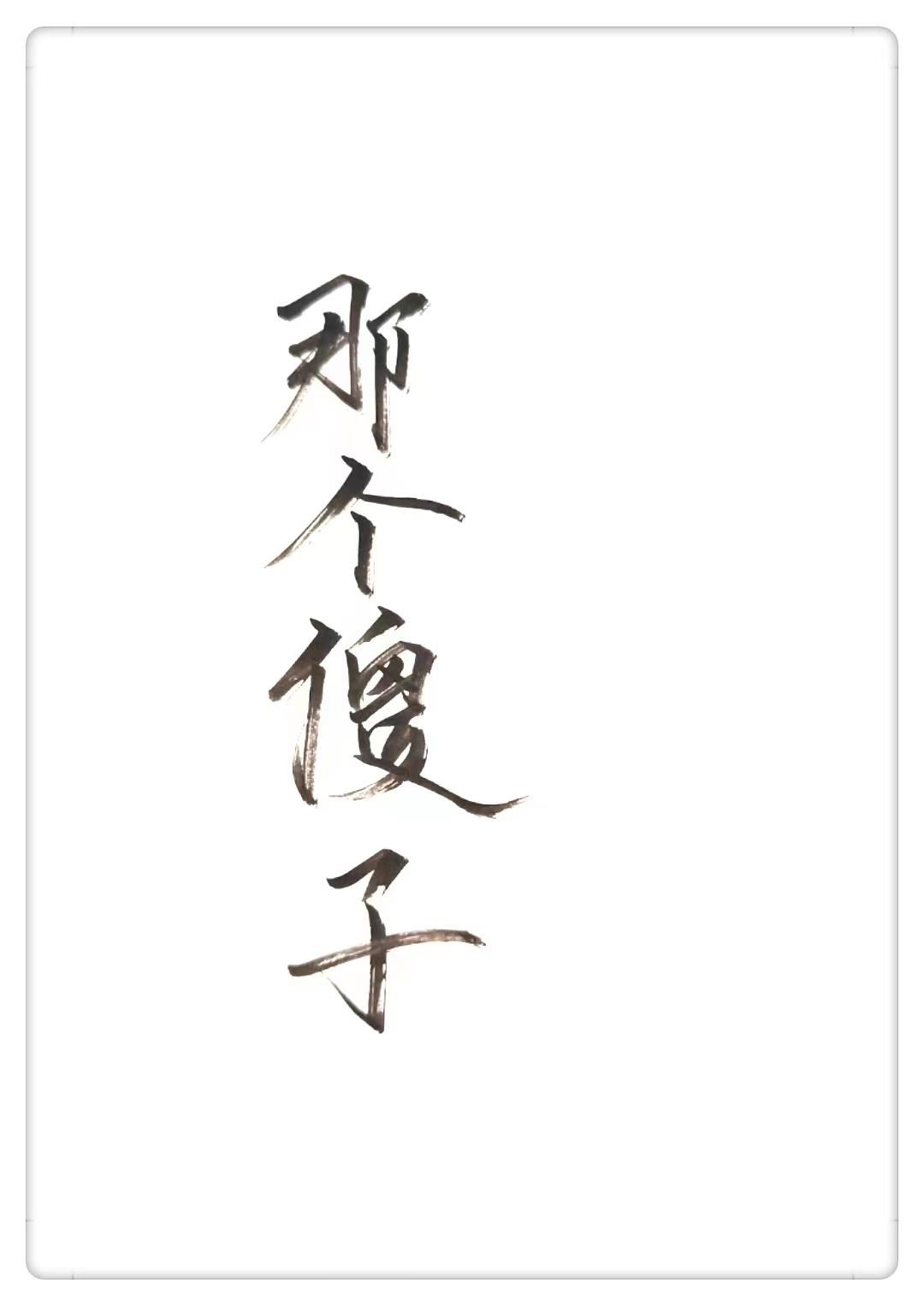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三打檀郎免费阅读 > 抉择(第2页)
抉择(第2页)
“不必了。”
阮夫人话音未落,几日不见的阮信推门走了进来,唬了阮夫人一跳。
一边埋怨丈夫走路没动静,一边给他倒茶,又吩咐秋禾去端碗绿豆银耳汤来。
拉着阮信坐下,又急急问,“老爷,你怎地说不必了?”
阮信回握住阮夫人的手,叫秋禾摒退下人、不必再来,好半晌却欲言又止。
阮夫人急得抽出手来,“绡儿怎么了?你快说啊,真要急死我不成!”
“绡儿……被人掳走了,可能是北戎人。”
“你说什么?”
“都怪我……”
阮信低了头,余下的话卡在了嗓子眼,说不出来。
阮夫人晃了晃身子,被他一手扶住,抬起头看时,只见一张脸没了血色,神情木然。
阮信从未见过夫人这般,铮铮汉子一条,眼眶先蓄了泪,“你……”
话未出口,阮夫人先开了口,声音无波,“几天了?”
“四天。”
“确定是北戎?”
“……十有八九。”
“要上报吗?”
阮夫人的眼神忽地灼热起来,她热切地看着阮信的眼睛,“老爷,上报朝廷吗?”
阮信被她的眼神烫得惭愧难当,别过头,不敢看她。
阮夫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刚才那一口气全都泄了,整个人瘫坐到地上,泪如泉涌。
“罢了,你只管做好的你的忠臣良将,我的绡儿可以没有爹,但不能没有娘!只求你徇私枉法一次,就将我们娘俩一并发落去庙里当了姑子,若是这也不行,好歹把孩子接回来,我们娘俩自行了断就是,绝不碍你的眼!”
“夫人!你、你这是
说什么话!”
阮信心中酸楚,伸手来拉阮夫人,被阮夫人一把推开。
他只得陪着阮夫人坐在地上,强力将她揽在怀里,低声说,“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此事瞒不住,若北戎人借着绡儿发难,大兵压境,朝廷如何不知?到时我就是想徇私情,众目睽睽之下,也作不得主。”
阮夫人忍了悲声,冷笑道,“上报又如何,朝廷提早知道了,你就能为了绡儿割城池让地了?”
凉州与北戎之间,十三道大小山脉,几百里皑皑雪原,白山黑水之上,哪一处没有浸染过大虞将士的热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如何能为一女子割让!
阮信默然半晌,道“我已写好奏折,言明幼女为山贼所掳,请皇上降罪,将冰绡退婚。”
“若是折子走得慢点,到圣旨传来凉州,半月过去,我和青时必将冰绡接回!绡儿脱了太子妃的身份,就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届时,战事若起,丢城割地、徇私枉法之罪,戴到战场上、用战功去抵便是!”
左不过,一家人丢了官,寻个穷乡僻壤过下半生罢了。
阮夫人听他这样说,心里更沉了几分。
她这丈夫上了战场智计无双,对上朝廷,想的却不是抉择利害的对策,而是忠孝两全之法。
阮夫人身为后宅妇人,也知道朝廷这些年虎视眈眈,正愁寻不到什么大错处,此事一出,岂能让阮信如意?
到时两道八百里加急传来,忠义
,儿女,性命,只怕什么都保全不了。
退一步说,即便事情真如阮信所料,到时两军对垒,北戎人将刀架在冰绡的脖子上,威胁凉州割地赔款,阮信真能如他所言,先把女儿赎回来,再去戴罪立功吗?
一面是凉州百姓和无数将士,一面是将军府不谙世事的小姐,阮信会如何选?阮夫人只能想到一位父亲的选择,却不敢猜测一方守将的抉择。
她这样想,不是怀疑阮信的人品,恰恰是因为太了解他那颗忠君报国的心,心里才更加不安。
若是青时主事……
若是青时主事,事情定然是另一种走向。
阮夫人不敢往下深想,止了眼泪,问道,“青时何时回来?”
阮信略一沉吟,“我已着人快马传信给他,大约后日。”
阮夫人拉过他的手,满眼哀戚,“老爷,我只求你这一次,等青时回来,再递折子不迟。”
阮信反握住夫人的手,神色凝重,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京娘,你可不要想岔了……”
夫妻二人一面心焦,一面惊心,沉默之间,三声急促的扣门声响起。
管家的声音传了进来,“老爷,夫人!有人递进来一封信,说是……说是和小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