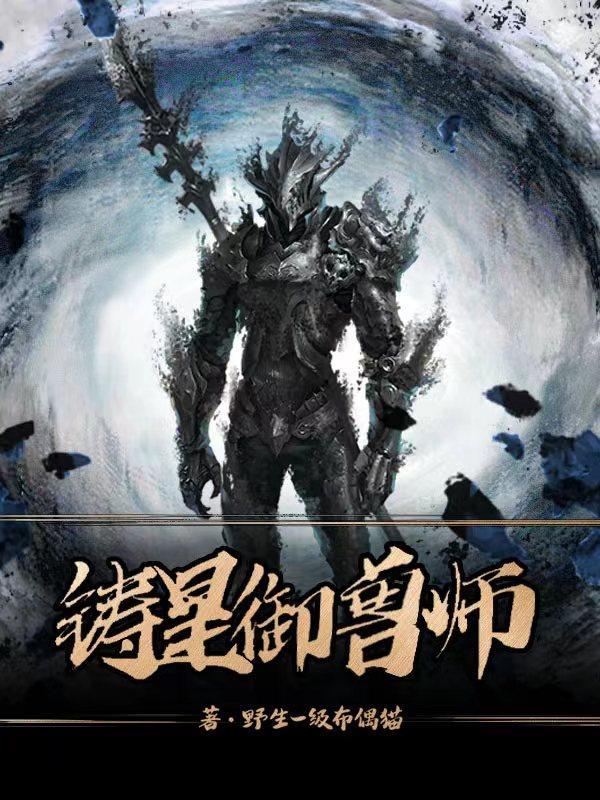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圣殿春秋三部曲 > 第79章(第3页)
第79章(第3页)
她迟疑了片刻,然后从头上脱掉睡袍。
他惊愕了。她通常是不那么快地脱掉衣服的。他明白了,她是让墨水弄得惊慌失措了。他盯着她赤裸的身体。她在女修道院发福了些:她的乳房比先前像是更大更圆了,她的小腹微显隆起,她的臀部有着一条诱人的翘起的曲线。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感到下身起来了。
她弯腰从铺石板的地面上用捆扎起来的睡袍抹去墨渍。她在擦地时,乳房抖动着。她转过身去,他看到了她丰满后身的全貌。若不是他对她了解至深的话
,准会疑心她想挑起他的欲火。但菲莉帕从来不想挑动任何人,更不消说他了。她只不过是狼狈不堪,尴尬至极罢了。而这恰恰更刺激了他在她拖地时盯着她暴露无遗的裸体。
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女人了,何况最后那个是索尔兹伯里的令人十分不满的妓女。
到菲莉帕站直身体时,他那家伙已经挺起了。
她看到他在盯着她看。“别瞅我,”
她说,“上床去吧。”
她把脏污的睡袍扔到待洗衣物的大篮子里。
她到衣橱跟前,打开了盖子。她去王桥时把她大部分服装都留在那里了:住在女修道院里,哪怕是贵族客人,也不宜穿得太绚丽的。她又找出了一件睡袍。在她把衣服拉出来时,拉尔夫的目光在她身上扫来扫去。他盯着她那高耸的乳房,覆盖着黑毛的隆起的阴部,他的嘴发干了。
她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你别碰我。”
她说。
要是她不这么说,他大概就会躺下睡觉了。但她这么迅捷的反应刺激了他。“我是夏陵伯爵,而你是我妻子,”
他说,“我想什么时候碰你就碰你。”
“你不敢。”
她说完就转过身去穿睡袍。
这一下可激怒了他。就在她举起衣服,想从头上套下去的时候,他抽了她屁股一巴掌。那是抽在光皮肤上的狠狠的一巴掌,他知道把她打疼了。她跳起来,还叫出了声。“这就叫不敢。”
他说。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
,嘴角露出反抗的意味,他冲动之下,挥拳打在她嘴上。她被打得后退几步,摔倒在地。她连忙用两只手去捂嘴,血从指间淌下。但她仰卧在地,浑身赤裸,大腿叉开。他能看到她腿裆处阴毛丛生的三角区,那道裂缝微张,看上去就像是在招迎。
他趴到了她身上。
她拼死推拒,但他比她块头大,而且孔武有力。他毫不费力地就制伏了她的抵抗。跟着他就进入了她的身体。她那儿很干,却不知为什么反倒让他激动。
很快就完事了。他喘着粗气,滚下她的身体。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她。她的嘴上有血。她并没有回望他;她的眼睛紧闭着。但他似乎看到她脸上有一种奇特的表情。他想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这时他比先前更感困惑了。
她看上去有些得意。
梅尔辛知道菲莉帕已经回到王桥,因为他看到她的侍女在贝尔客栈里。他期待着他的情人能在当晚到他住处来,结果却失望了——她没有来。他觉得,她无疑是感到尴尬了。没有一位女士在做了她这种事后会舒服的,哪怕有着不得已的理由,哪怕她热恋的男人知情并理解。
又一个晚上过去了,她还是没露面。随后到了礼拜天,他肯定会在教堂见到她。可是她没来祈祷。一位贵族缺席礼拜天的弥撒简直闻所未闻。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她呢?
祈祷之后他打发洛拉跟阿恩和埃姆一起
回家,然后便穿过绿地,来到旧医院。楼上有为重要客人备下的三个房间。他上了户外楼梯。
在走廊里他与凯瑞丝面对面地相遇了。
她并没有劳神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伯爵夫人不想让你见她,不过你倒大概该去见她。”
她说。
梅尔辛注意到她说话的古怪次序:不是“伯爵夫人不想见你”
,而是“伯爵夫人不想让你见她”
。他看着凯瑞丝手里的盆。里面有一块血染的布片。他心里一怕。“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凯瑞丝说,“婴儿无妨。”
“感谢上帝。”
“你是那婴儿的父亲,不用说了?”
“请你千万别让别人听到你这话。”
她面带哀伤:“这些年来你我都在一起,而我只怀过一次孕。”
他移开了目光:“她住在哪个房间?”
“对不起,我谈起了我自己。我是你最没兴趣的人了。菲莉帕女士在中间那个房间。”
他虽然惦记着菲莉帕,但还是注意到了她声音中压抑不住的凄凉,便停下了脚步。他触了触凯瑞丝的胳膊。“请不要认为我对你没有兴趣,”
他说,“我始终关心着你的事和你是不是高兴。”
她点点头,泪水涌进了她的眼睛。“我知道,”
她说,“我太自私了。去看看菲莉帕吧。”
他离开了凯瑞丝,走进了中间那房间。菲莉帕正跪在祷告台前,背对着他。他打断了她的祈祷。“你没事吧?”
她站起来
,转过身面对着他。她的脸上乌七八糟。她的嘴唇肿得有平日的三倍,还结着厚痂。
他猜想,凯瑞丝给她洗过了伤口——所以盆里的布片上才有血迹。“出什么事了?”
他说,“你还能讲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