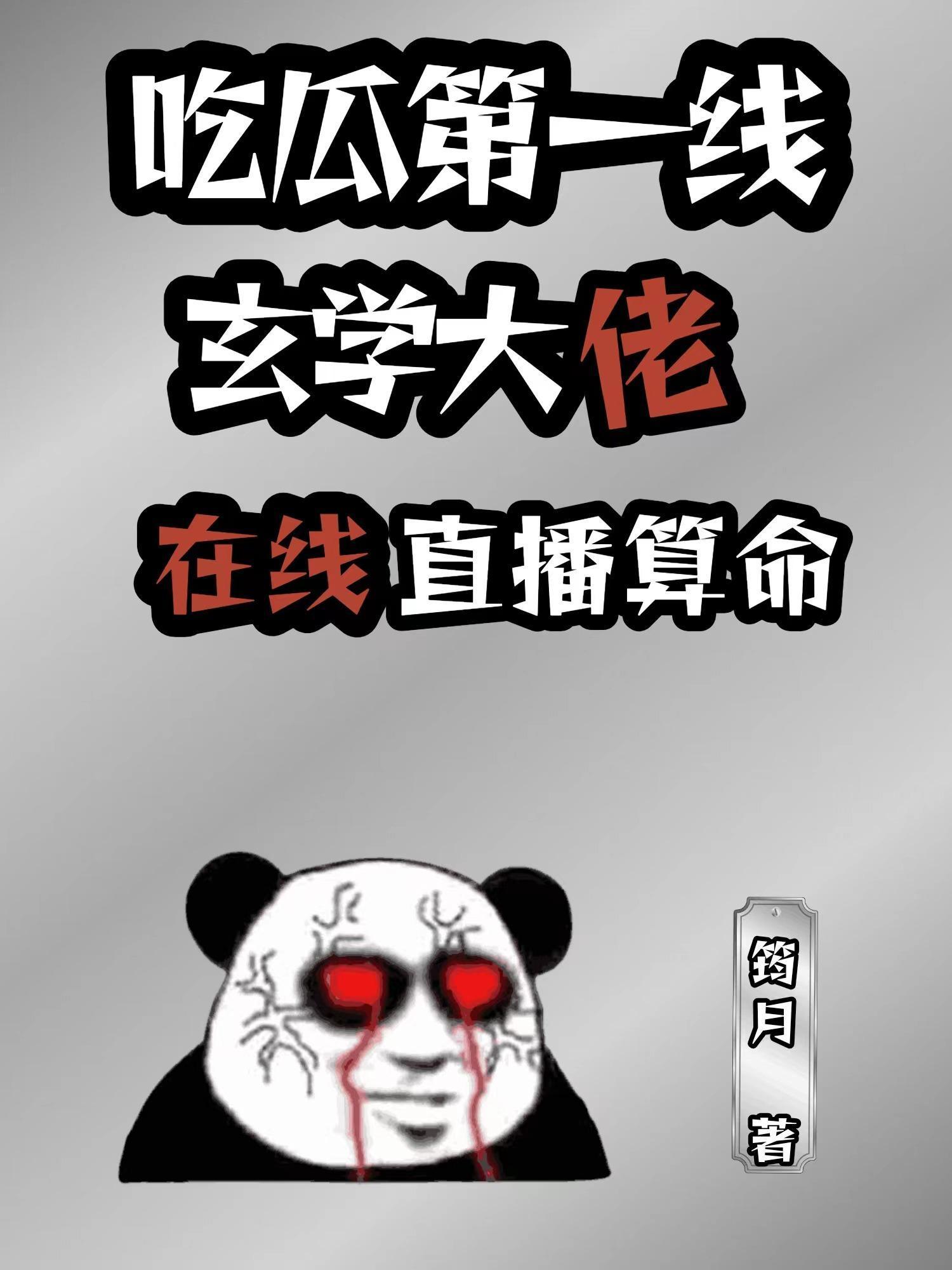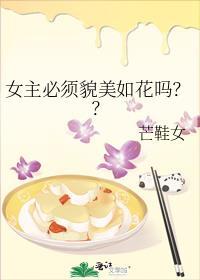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圣殿春秋三部曲 > 第62章(第4页)
第62章(第4页)
过了一会儿,他才穿过回廊,进入医院。
修女们簇拥在圣坛前架起的一张床边。她们一定有个重要的病人,他心想。他不知道那是谁。一个看护修女转过来面对着他。她的口鼻上戴着面罩,但他从他和他们家人都有的那双闪着金光的碧眼中认出来:她是凯瑞丝。尽管他只看得到她的一小部分面孔,还是在她的眼神中注意到了一种古怪的表情。他本想看到厌恶和轻蔑,结果却是悲悯。
他怀着惶惑的心情走近床边。别的修女看到他都敬畏地向边上移
开了。跟着,他就看到了病人。
是他母亲。
彼得拉妮拉的大脑袋躺在一个白枕头上。她在出汗,从鼻孔中一直向外淌一细道鲜血。一个修女在抹去血迹,但随抹随流。另一个修女给病人端来一杯水。彼得拉妮拉皱巴的脖颈皮肤上有一片紫色皮疹。
戈德温像挨了打似的哭出了声。他恐惧地瞪着眼睛。他母亲用难过的眼神盯着他。不消怀疑了:她已倒在了黑死病的危害中。“不!”
他号叫着,“不!不!”
他感到胸口有一阵难忍的痛楚,如同被捅了一刀。
他听到身边的菲利蒙用恐惧的声音说:“保持镇静啊,副院长神父。”
可他做不到。他张开嘴想尖叫,但出不来声。他突然感到魂飞魄散,控制不了行动了。随后,地上升起一团黑雾,吞噬了他,把他的躯体渐渐吞没,直到他的口鼻之上,使他无法呼吸,随后又升到他的眼睛,使他眼前一团漆黑;他终于失去了知觉。
戈德温在床上躺了五天。他没有进食,只是在菲利蒙把杯子凑到他嘴边时才喝一点水。他无法正常思考。他也不能动,似乎是没办法决定做什么。他抽泣着入睡,醒来再接着抽泣。他模糊地感到一个修士触摸他的额头,取了尿样,诊断为脑炎,并为他放了血。
后来,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满脸惊恐的菲利蒙给他带来了消息:他母亲死去了。
戈德温起了身。他给自
己刮了脸,穿上一件新袍服,前往医院。
修女们已为尸体洗净穿衣完毕。彼得拉妮拉的头发梳理整齐,身穿一件昂贵的意大利绒裙。看到她面孔死白,双目紧闭的样子,戈德温感到让他躺倒的那种痛楚又出现了,但这一次他能顶住了。“把她的遗体送到大教堂去吧。”
他吩咐道。通常,陈尸于大教堂是只有修士、修女、高级教士和贵族才有的荣誉,但戈德温知道,没人会斗胆反对他这样做。
当她被送进教堂,放到圣坛前面之后,他跪倒在她身边,祈祷着。祷告帮他平息了恐惧,他逐渐理清了该做些什么。等他站起来的时候,便吩咐菲利蒙马上在会议厅召开一次会议。
他觉得浑身颤抖,但他知道必须振作起来。他一向擅长说服别人,现在他要把这种能力用到极致。
修士们集合好之后,他给他们读了《创世纪》中的一段。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note"
src="
m。cmread。wfbrdnewbooks189050511569050oebpschapter83imagesnote。jpg"
data-der-atmosid="
5527c1c8a6e2eb92056a5f409e4c8805ec797a7ab256"
data-der-srcbackup="
imagesnote。jpg"
>#pageNote#0
戈德温从书上抬起眼。修士们都神情专注地凝视着他。他们都熟知亚伯拉罕和以撒的
故事。他们更大的兴趣在他,戈德温的身上。他们警觉而谨慎,不知下一步是什么。
“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教导了我们什么呢?”
他为制造效果反诘道,“上帝让亚伯拉罕杀死他的儿子——不但是他的长子,而且是他的独子,在他年届一百时把儿子烧死。亚伯拉罕反对了吗?他请求开恩了吗?他跟上帝争辩了吗?他指出了杀死以撒是谋害,是杀子,是可怕的罪孽了吗?”
戈德温让这个问题悬念一会儿,然后低头看书,又读道:“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
他又抬起头来:“上帝也会试验我们。他可能命令我们进行看似错误的做法。也许他会要我们去做看似罪孽的事情。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牢记亚伯拉罕。”
戈德温讲话时用的是他所知的他最具说服力的布道方式,顿挫有致又娓娓动听。他从八边形的会议厅中一片静谧看得出,他已经攫住了他们全神贯注的注意力:没人骚动,没人交头接耳,也没人不安。
“我们不该询问,”
他说,“我们不该争论。当上帝引导我们时,我们都应该追随——他的愿望,无论在我们无力的头脑中看似多么愚蠢,多么罪过,或多么残忍。我们懦弱而卑微。我们的理解力低下。不该由我们做出决定或选择。我们的职责很简单。那就是服从。”
随后他告诉了他们,他们要怎么做。
天黑之
后,主教到达了。当队伍进入修道院地界时,已经快到半夜了:他们由火把伴随。修道院中的人已经入睡了几个小时,但还有一伙修女在医院中上班,其中一个跑来叫醒凯瑞丝。
“主教到了。”
她说。
“他找我干吗?”
凯瑞丝睡眼惺忪地问。
“我不知道,副院长嬷嬷。”
她当然不知道。凯瑞丝赶紧起床,披上一条斗篷。